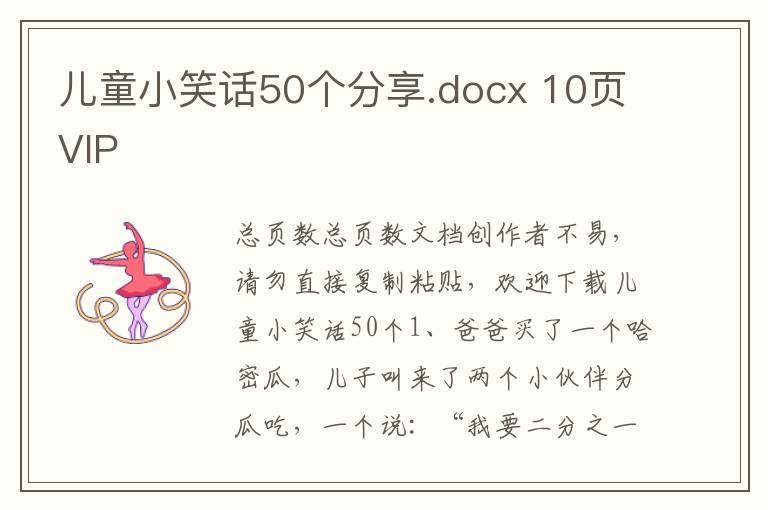抗戰相聲,老舍原來還是個段子手

抗戰陪都重慶有一個抗戰曲藝潮,其中的“抗戰相聲”堪稱重慶特產,像毛肚火鍋一樣誕生于重慶,還有老舍這樣的大名家親自上陣支持,還產生了歐少久、董長祿(小地梨)師徒這樣的抗戰相聲名家,今天我們說說當時老舍在重慶說相聲和寫相聲的故事。
票友
據《老舍年譜》所載史料,1938年8月老舍先生從淪陷的武漢撤退到重慶,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1946年2月底赴美講學,抗戰時期老舍在重慶呆了近8年。
老舍在重慶先后住在大梁子青年會、白象街88號《新蜀報》和南泉,1943年最后搬到北碚蔡鍔路24號(現天生新村63號附16號)小樓。
老舍北碚舊居
這里原是林語堂買的房子,他到美國去了,就送給老舍住。老舍在此住得最久,寫了一代名著《四世同堂》前兩部《惶惑》和《偷生》,還寫了一籮筐話劇、散文、雜文、曲藝、詩詞,相聲雖然不是最多,但卻最有年代感。
1945年,老舍攝于重慶北碚寓所外。
我在北平有一位朋友,是個票友。此人這京戲呀,迷得厲害,一心想“下海”,成名角兒。可他是個左嗓子,唱得太差,誰聽了誰捂耳朵。沒辦法,只好自個兒找個清靜的地界兒——跑到西山去唱。上了裝,提把青龍偃月刀,連做帶打,唱關云長《單刀赴會》。正唱著,打山上下來一個老頭兒,打柴的樵夫。一看這位,嚇蒙了:不知是關老爺顯圣,還是土匪劫道,趕忙跪下磕頭:“好漢爺饒命!好漢爺饒命!”票友一看,心中暗喜,大喝一聲:“老頭兒休怕!饒爾等性命不難,只須——聽我一段西皮倒板——便可免你不死”。隨即便又野唱起來。但唱著唱著,樵夫“撲通”一聲又跪下了:“好漢爺,你甭唱了,還是殺、殺了我吧!”票友驚問:“為何?”老頭哭道:“我覺得,還是殺了我更好受”。老舍是一個老資格的相聲票友了。1924年去倫敦講學,也把相聲帶去,和中國同學演過傳統段子《大保鏢》、《黃鶴樓》,可能是相聲在英國最初的表演記錄。1930年他回國先后在齊魯大學、山東大學任教。據《齊魯晚報》2015年01月29日李耀曦《老舍在齊魯大學說相聲》一文回憶:齊大國文系1933級學生張昆河先生親口講述,老舍在一次師生聯歡會上打了一趟很接地氣的山東查拳后,就登臺開說單口相聲《票友》,笑翻全場——
2006年央視春晚侯耀華和郭達演的一個小品《戲迷》,構思和“包袱”,都跟老舍當年說的《票友》撞上了,可能他們都“偷”的是同一個相聲老段子。
敲頭
梁實秋先生《憶老舍》一文就寫了他和老舍在北碚說相聲的故事。
抗戰后,梁實秋差不多和老舍同時到重慶,主持《中央日報·平明副刊》,在國立編譯館上班。他對老舍的語言很贊:“只覺得他以純粹的北平土語寫小說頗為別致。北平土語,像其他主要地區的土語一樣,內容很豐富,有的是俏皮話、歇后語,精到出色的明喻暗譬,還有許多有聲無字的詞字。”
他還白描了老舍的戰時形像:“他又黑又瘦,甚為憔悴,他身體不大好,患胃下垂,平常總是佝僂著腰,邁著四方步,說話的聲音低沉,徐緩,但是有風趣……生活當然是很清苦的……老舍對誰都是一樣的和藹親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緣好,但是內心卻很孤獨。”“他離開北碚不久有一封信給我,附近作律詩六首,詩寫得不錯,可以從而窺見他的心情,他自嘆中年喜靜,無錢買酒,半老無官,文章為命,一派江湖流浪人的寫照。”
老舍和梁先生在北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作說相聲時,是快樂的,也是驚險的。那是北碚一個募款勞軍晚會,梁先生出面邀請清同治年間著名昆曲正旦錢金福的弟子姜作棟,和沈從文的小姨妹、禮樂館多才多藝的張充和,合演昆曲《鐵冠圖》的一個折子戲《刺虎》,“在這一出戲之前,要墊一段對口相聲。這是老舍自告奮勇的。蒙他選中了我做搭檔,頭一晚他 逗哏 我 捧哏 ,第二晚我 逗哏 他 捧哏 。事實上,掛頭牌的應該是他。他對相聲特別有研究。在北平長大的,誰沒有聽過焦德海、草上飛?但是能把相聲全本大套的背誦下來,則并非易事。”
老舍給他面授了說相聲的訣竅,還順手把兩個段子寫出來,一段是《新洪羊洞》,一段是《一家六口》,都是老相聲。“相聲里面的粗俗玩笑,例如 爸爸 二字剛一出口,對方就得趕快順口答腔地說聲 啊 ,似乎太無聊,但是老舍堅持不能刪免,據他看,相聲已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不可稍有損益。”
但有一點老舍還是讓了步:里面有一個規定動作,逗哏老舍要用折扇敲打捧哏梁的頭一下。“是我堅決要求,他才同意在用折扇敲頭的時候只要略為比劃而無需真打。
到了上演那一天,我們走到臺的前邊,泥塑木雕一般繃著臉肅立片刻,觀眾已經笑不可抑。”
但到該用折扇敲頭的時候,梁先生發現老舍“不知是一時激動忘形,還是有意違反諾言”,掄起大折扇狠狠地向自己打來,顯然是老舍為了相聲藝術,決定犧牲梁實秋:“我看來勢不善,向后一閃,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鏡,說時遲,那時快,我手掌向上兩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來的眼鏡,我保持那個姿勢不動,喝彩聲歷久不絕,有人以為這是一手絕活兒,還高呼: 再來一回! ”
月餅
據曾與侯寶林合著《曲藝概論》的相聲理論家汪景壽先生《老舍和相聲的緣分》一文考證:1938年8月老舍一到重慶,就舉辦了兩期通俗文藝講座,先后創作了《盧溝橋戰役》、《臺兒莊大捷》、《維生素》、《新對聯》、《歐戰風云》、《罵汪精衛》等相聲段子,和流亡到重慶的北方相聲演員歐少久、董長祿(小地梨)師徒在書場里表演,很受歡迎。
1939年春天,在重慶電影制片廠聯歡晚會上,老舍親自登臺與歐少久表演相聲《中秋月餅》,又加演一段老舍編寫的相聲《繞口令》,效果爆棚,引起《大公報》的關注,稱這些節目為“抗戰相聲”。
《繞口令》今已失傳,相聲《中秋月餅》后來由歐少久口述、殷文碩記錄整理,編入了《老舍文集》第13卷,并注:相聲《中秋月餅》是老舍于1938年在重慶編寫的。
《中秋月餅》定場詩引用一首民間小調:“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落在街頭?”然后利用月餅的傳統餡料味型比如五仁、豆沙、棗泥、叉燒、火腿、洗沙來抖包袱,把時政主旋律和傳統相聲的諧音手法巧妙結合,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罪行——
乙:您把月餅餡子,又比喻什么呢?
甲:我略舉幾種,比如:“五仁”——就是說日寇侵華罪行,慘無人(五仁)道……
日寇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從月餅餡子里,都能看出來……“豆沙”——見人“都殺”;“洗沙”(洗殺)——洗劫一空,再來殺害;“棗泥”,就是把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糟(棗)蹋得和泥(泥)土一樣……
乙:太可恨了……
歐少久、董長祿(小地梨)師徒,帶著這段把美食和戰爭一鍋燴的相聲,在成渝等地巡演,到處爆棚,曾遭有關當局禁演。
精心遴選,每日推送,歡迎打開微信,搜索公眾號“長城曲藝網”,更多精彩,不見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