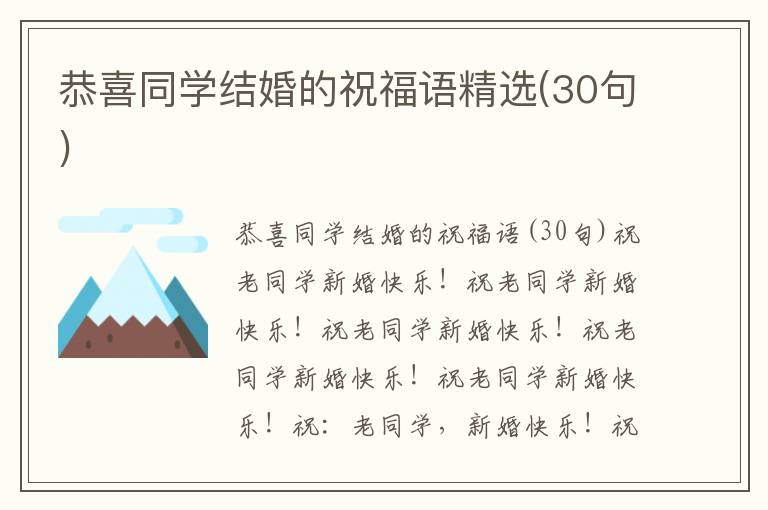結婚就是成親,就是成為親人了

乍然驚醒,已是早上八點半。連滾帶爬從床上蹦起來,沖到衛生間洗漱,又沖到臥室換衣服,卻怎么都找不到我昨天放在床頭的內衣。
沒辦法,只好從抽屜里拿出一件干凈的換上,匆忙往學校趕。我教畢業班語文,九點鐘有一節課,不吃早飯的話,應該能趕上。
當初為了照顧我的工作,我和蔣銘的婚房特意買在學校附近,走路十多分鐘也就到了。我邊朝學校走,邊給蔣銘發微信,問他有沒有看見我的內衣。
他很快就回復我了:“我帶走了,想你的時候拿出來用。”
我臉有些紅,真虧他想得出來。
“南京離北京不遠的,你周末可以坐高鐵回來。”我說。
這句話是他昨天說的,我舍不得他走,哭到凌晨四點,他不停安慰我,到后來困極了,就把這句話和“暑假好幾個月呢,你到北京,咱倆就在一起了”輪換著反復說。
他昨天用這句話安慰我,今天我又拿這句話哄他,不過是為了讓彼此的心情好一點。
我的微信發過去很久,蔣銘才回復:“乖,我們都要好好的。”
這時候我已經到學校了,就懶得再回復他了。
仔細想來,我和蔣銘一直是不同的。
才談婚論嫁時,提起我的工作,他總是說,初中教師挺好的,能讓他在拼搏的時候,有一個穩定的后方。我們結婚后沒多久他就升職了,從普通的銷售員升到了銷售經理。他又說,等他做了總監,我就辭掉這份操賣白粉心掙賣白菜錢的雞肋工作,跟著他吃香喝辣。那時候我總笑笑不說話,我以為他不過是安慰我工作辛苦。
現在想來是我誤會了,他確實是嫌我工作操心錢又少。
蔣銘所在的公司,高層職位基本都被元老們壟斷了。像他這樣的生力軍,想要升到總監是非常困難的。他之前還計劃著跳槽,卻一直沒有找到更好的。直到兩周前,公司老板問他,愿不愿意去北京開拓市場。到時候,他的職位,可能就不止是總監了。
蔣銘很心動,來問我的意見。我當然不愿意他去北京。我們現在雖然不富裕,但好歹有房有車,每天生活在一起不好嗎?蔣銘卻說,其實,錢都是次要的,他主要想試試看,拼搏一下的話,能做到什么程度。
蔣銘說,他不想三十歲生日還沒過,就困守一隅以養老。
我忍不住冷笑,既然都想好了,還問我干嗎?明著是尊重我的意見,實際上不過是通知我一聲。
我們冷戰了兩個星期。我很生氣,氣他不為我們兩個人考慮。我本來想著,帶完這個畢業班就要小孩,他這一走,計劃全打亂了。
這兩個星期,蔣銘一直賠著小心。我知道他是在意我的,不然不會這樣做小伏低。我就是生氣,氣他把所謂的“夢想”放在我前面。最后兩天的時候,我原諒他了,他是男人,有所追求理所應當,我不該因為我們是夫妻,就絆住他的腳步。
那么,婚前沒有體會過的異地戀,就讓我們婚后體驗一下好了。都說小別勝新婚,但愿如此。
然而真正分居兩地,我才知道,我把一切都想得過于美好了。
一開始,我們每天至少三個電話。起床時,我打給他,撒會兒嬌,說“老公我起床了”。中午吃食堂,我告訴他今天的糖醋排骨味道還不錯。晚上洗完澡躺床上,跟他煲電話粥,把這一天發生的事情細細說給他聽,就像他仍在我身邊一樣。
我是想要去看他的,但我們總沒時間,算下來,我們已經兩個月沒見了。那天我下定決心,這個周末,無論如何也要抽出時間去北京見他。哪怕他白天還是很忙,我只要晚上能見到他就好。
我的到來,讓蔣銘非常高興。見到我的那一瞬間他眼睛里的光,就像我們第一次見面。
是的沒錯,我倆是一見鐘情。若不是足夠愛,性格如此不同的人,又怎么能走進婚姻,且每日甜如蜜呢!離開北京時,我又哭了,沒辦法,我就是眼淚多,受不了分別。
回去沒多久我就病了,倒不是什么大病,不過是發了場高燒而已。以前不是沒發過燒,但從來不是一個人。
我躺在床上,燒得昏昏沉沉,想喝水,只能掙扎著起來倒。手是軟的,一杯水掉地上,燙傷了我的腳。我號啕大哭,打電話給蔣銘,不求別的,哪怕他安慰我兩句也好。卻不料,他掛斷了我的電話,只發來一條短信:“我在開會,待會兒打給你。”
我擦干眼淚,拿牙膏處理完燙傷,躺床上不肯睡,怕睡著了接不到他的電話。卻不料,一直等到晚上他才打來。
他的聲音很疲憊,我指責的話語,一句都說不出來。
病好之后,我突然發現,我好像沒那么依賴他了。即使他不在,好像也沒什么。欣喜憂愁不能第一時間分享,歡笑落淚不能給我一個擁抱,隔著電話再親密,日子還是得一個人過。我想和他白頭偕老,我也想要眼前的這兩年,可他不能給我。
我不知道蔣銘有沒有注意到,我主動打給他的電話變少了。我們之間的聯系調了個個兒,一開始,是我每天打無數個電話給他;到后來,我幾乎不主動聯系他了,都是他打給我。
大家都忙,這大半年,我們總共才見了兩三次面。好在有暑假,那幾個月,我在北京,日日陪著蔣銘。恍惚間我誤以為,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
學校規矩,帶完初三,第二年從初一開始帶,這樣跟孩子們的感情會好些。卻不料,因為頭一年我帶出來的班中考成績太好,而新升上來的畢業班,語文老師資歷不夠,我被學校安排再帶一屆畢業班。
聽到這個消息,我還沒多大反應,蔣銘怒了,帶畢業班預示著我們沒多少時間見面。他說:“辭職吧寶貝兒,我現在的收入養得了你。大不了,每個月我給你發工資。”
可是,那也是我的事業呀!
新的學年,蔣銘一天給我打一個電話;到后來,變成三天一個;再后來,就是一周一個。我們好像變得越來越生疏了。
我突然懷孕了。若換作以前,我會很高興,我和蔣銘的年齡,是時候要個孩子了。可是現在我卻有些難受,蔣銘不在身邊,我要一個人度過整個孕期嗎?我還帶著畢業班呢!
我問蔣銘什么時候回來,若他一年之內能回來的話,我就留下這個孩子,孕期一個人我或許還能忍受,孩子生了還是我一個人,這個怎么都接受不了的。
蔣銘卻問我,什么時候辭職去北京。
我當然不會辭職。
懷孕本來是一件挺好的事,但到我和蔣銘這里,卻變成了吵架的導火索。
最后一次不歡而散后,我扔了手機,趴床上哭了幾個小時。
孩子就是這時候沒的。
蔣銘請假回來照顧我,卻整日板著臉,就好像我欠了他很多錢。
一直到他走,我們都沒有和好。
我心里很冷。我還愛他,可我不知道該怎么愛他了。我有預感,若我們這種兩地分居的狀態不改變,婚姻遲早會走向盡頭。我舍不得。因著這份舍不得,我下定了決心:帶完這屆畢業班就辭職。因著這份舍不得,我必須得做點什么事情,來彌補我們的關系。我調整了補課時間,盡量把周末空出來,好到北京和蔣銘團聚。可是就算這樣,我們還是聚少離多。
那天,我到蔣銘住處的時候,他還沒回來。我用他留給我的鑰匙開了門。床頭柜上扔了幾件臟衣服,我順手拿來幫他洗掉。卻不料,在那臟衣服下,發現了一件紫色的內衣。那內衣不是我的。
我手腳冰涼,站了很長時間,才找回一點點腦子。我開始翻蔣銘的衣柜,不出所料,我又看見了好幾件陌生的內衣,有些還是成套的。
眼淚奪眶而出,我拿著包就離開了,北京我待不下去,我要回到我南京的家,那里,起碼沒有陌生的女人內衣。
蔣銘打了無數個電話,我都沒接,后來,我干脆關機了。
半夜我才回到家,累極了。打開門,卻發現家里的燈亮著,嚇一跳,以為屋漏偏逢連夜雨,不小心招了賊。
正忐忑間,蔣銘從屋子里走了出來。他說:“傻瓜,那些內衣都是買給你的,只是一直忘了拿回來給你。你怎么那么傻,也不仔細看一看,全都是你的尺寸。”
又過了一個月,蔣銘回來了,他辭職了,決定回來創業。他跟我說,并不是最好的時機,可是他畢竟結了婚,結婚就是成親,就是成為親人了。若因為自己的夢想讓親人不開心、受委屈,夢想還有什么意義?更何況,出走兩年,該體驗的也都體驗到了,是時候在一起白首不相離了。
我突然發現,其實,我并不是很了解蔣銘,起碼,沒有我想象的那么了解。但我知道,他愛我,而我也愛他如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