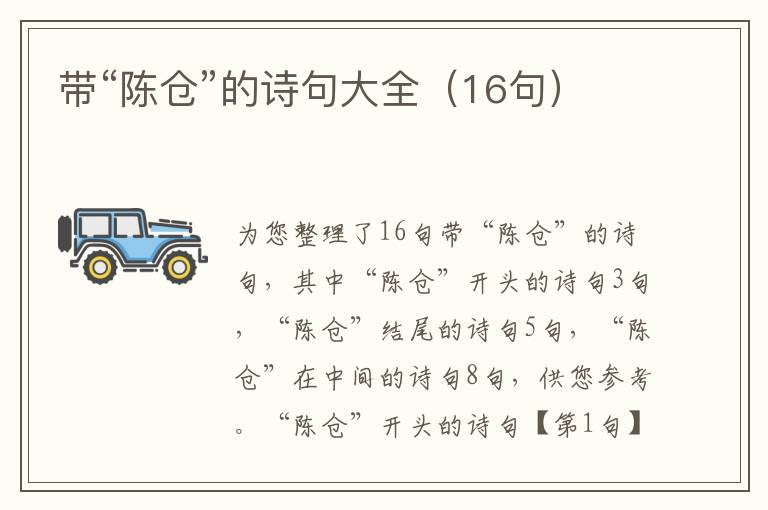多和爹娘說(shuō)說(shuō)話原唱完整版匯編100句

莫言作品《枯河》
一輪巨大的水淋淋的鮮紅月亮從村莊東邊暮色蒼茫的原野上升起來(lái)時(shí),村子里彌漫的煙霧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種凄艷的紅色。這時(shí)太陽(yáng)剛剛落下來(lái),地平線上還殘留著一大道長(zhǎng)長(zhǎng)的緊云。幾顆瘦小的星斗在日月之間暫時(shí)地放出蒼白的光芒。村子里朦朧著一種神秘的氣氛,狗不叫,貓不叫,鵝鴨全是啞巴。月亮升著,太陽(yáng)落著,星光熄滅著的時(shí)候,一個(gè)孩子從一扇半掩的柴門中鉆出來(lái),一鉆出柴門,他立刻化成一個(gè)幽靈般的灰影子,輕輕地飄浮起來(lái)。他沿著村后的河堤舒緩地飄動(dòng)著,河堤下枯萎的蓑草和焦黃的楊柳落葉喘息般地響著。他走得很慢,在枯草折腰枯葉破裂的細(xì)微聲響中,一跳一跳地上了河堤。在河堤上,他蹲下來(lái),籠罩著他的陰影比他的形體大得多。直到明天早晨他像只青蛙一樣蜷伏在河底的紅薯蔓中長(zhǎng)眠不醒時(shí),村里的人們圍成團(tuán)看著他,多數(shù)人不知道他的歲數(shù),少數(shù)人知道他的名字。而那時(shí),他的父母全都目光呆滯,猶如魚類的眼睛,無(wú)法準(zhǔn)確地回答鄉(xiāng)親們提出的關(guān)于孩子的問(wèn)題。他是個(gè)黑黑瘦瘦,嘴巴很大,鼻梁短促,目光彈性豐富的從來(lái)不知道什么叫生病的男孩子。他攀樹的技能高超。明天早晨,他要用屁股迎著初升的太陽(yáng),臉深深地埋在烏黑的瓜秧里。一群百姓面如荒涼的沙漠,看著他的比身體其他部位的顏色略微淺一些的屁股。這個(gè)屁股上布滿傷痕,也布滿陽(yáng)光,百姓們看著它,好像看著一張明媚的面孔,好像看著我自己。
他蹲在河堤上,把雙手夾在兩個(gè)腿彎子里,下巴放在尖削的膝蓋上。他感到自己的心像只水耗子一樣在身體內(nèi)哧溜哧溜地跑著,有時(shí)在喉嚨里,有時(shí)在肚子里,有時(shí)又跑到四肢上去,體內(nèi)仿佛有四通八達(dá)的鼠洞,像耗子一樣的心臟,可以隨便又輕松地滑動(dòng)。月亮持續(xù)上升,依然水淋淋的,村莊里向外膨脹著非煙非霧的氣體,氣體一直上升,把所有的房屋罩進(jìn)下邊,村中央那棵高大的白楊樹把頂梢插進(jìn)迷蒙的氣體里,挺拔的樹干如同傘柄,氣體如傘如笠,也如華蓋如毒蘑菇。村莊里的所有樹木都瑟縮著,不敢超過(guò)白楊樹的高度,白楊樹驕傲地向天里站,離地二十米高的枝丫間,有一團(tuán)亂糟糟的柴棍,柴棍間雜居著喜鵲和烏鴉,它們每天都爭(zhēng)吵不休,如果月光明亮,它們會(huì)跟著月亮噪叫。
或許,他在一團(tuán)陰影的包圍中蹲在河堤上時(shí),曾經(jīng)有抽泣般的聲音從他干渴的喉嚨里冒出來(lái),他也許是在回憶剛剛過(guò)去的事情。那時(shí)候,他穿著一件肥大的褂子,赤著腳,站在白楊樹下。白楊樹前是五問(wèn)全村唯一的瓦房,瓦房里的孩子是一個(gè)很漂亮的小女孩,漆黑的眼睛像兩粒黑棋子。女孩子對(duì)他說(shuō):“小虎,你能爬上這棵白楊樹嗎?”
他怔怔地看著女孩,嘴巴咧了咧,短促的鼻子上布滿皺紋。
“你爬不上去,我敢說(shuō)你爬不上去!”
他用牙齒咬住了厚厚的嘴唇。
“你能上樹給我折根樹杈嗎?就要那根,看到了沒(méi)有?那根直溜的,我要用它削一管槍,削好了咱倆一塊耍,你演特務(wù),我演解放軍。”
他用力搖搖頭。
“我知道你上不去,你不是小虎,是只小老母豬!”女孩憤憤地說(shuō),“往后我不跟你耍了。”
他用很亮的黑眼睛看著女孩,嘴咧著,像是要哭的樣子。他把腳放在地上搓著,終于干巴巴地說(shuō):“我能上去。”
“你真能?”女孩驚喜地問(wèn)。
他使勁點(diǎn)點(diǎn)頭,把大褂子脫下來(lái),露出青色的肚皮。他說(shuō):“你給我望著人,俺家里的人不準(zhǔn)我上樹。”
女孩接過(guò)衣裳,忠實(shí)地點(diǎn)了點(diǎn)頭。
他雙腳抱住樹干。他的腳上生著一層很厚的胼胝,在銀灰色的樹干上把得牢牢的,一點(diǎn)都不打滑。他爬起樹來(lái)像一只貓,動(dòng)作敏捷自如,帶著一種天生的素質(zhì)。女孩抱著他的衣服,仰著臉,看著白楊樹慢慢地傾斜,慢慢地對(duì)著自己倒過(guò)來(lái)。恍惚中,她又看到光背赤腳的男孩把粗大的白楊樹干墜得像弓一樣彎曲著,白楊樹好像隨時(shí)都會(huì)把他彈射出去。女孩在樹下一陣陣發(fā)顫。后來(lái),她看到白楊樹又倏忽挺直。在漸漸西斜的深秋陽(yáng)光里,白花花的楊樹枝聚攏上指,瑟瑟地彈撥著淺藍(lán)色的空氣。凍一樣澄澈的天空中,一綹綹的細(xì)密楊枝飛舞著;殘存在枝梢上的個(gè)把楊葉,似乎已經(jīng)枯萎,但暗藍(lán)的顏色依舊不褪;隨著枝條的擺動(dòng),枯葉在窸窣作響。白楊樹奇妙的動(dòng)作繚亂了女孩的眼睛,她看到越爬越高的男孩的黑色般的脊梁上,閃爍著鴉翅般的光翠。
“你快下來(lái),小虎,樹要倒了!”女孩對(duì)著樹上的男孩喊起來(lái)。男孩已經(jīng)爬進(jìn)稀疏的白楊樹冠里去了,樹枝間有鴉鵲穿梭飛動(dòng),像一群碩大的蜜蜂,像一群陰郁的蝴蝶。
“樹要斷啦!”女孩的喊聲像火苗子一樣燒著他的屁股,他更快地往上爬。鴉鵲翅膀扇起的腥風(fēng)直吹到他的脖頸子里,使他感到脊梁溝里一陣陣發(fā)涼。女孩的喊叫提醒了他,他也覺(jué)得樹干纖細(xì)柔弱,彎曲得非常厲害,冰塊一樣的天空在傾斜著旋轉(zhuǎn)。他的腿上有一塊肉突突地跳起來(lái),他低頭看著這塊跳動(dòng)的肌肉,看得清清楚楚。就在這時(shí)候,他又聽到了女孩的叫聲,女孩說(shuō):“小虎,你下來(lái)吧,樹歪倒了,樹就要歪到俺家的瓦屋上去了,砸碎俺家的瓦,俺娘要揍你的!”他打了一個(gè)愣怔,把身體貼在樹干上,低眼往下看。這時(shí)他猛然一陣頭暈眼花,他驚異地發(fā)現(xiàn)自己爬得這樣高。白楊樹把全村的樹都給蓋住了,猶如鶴立雞群。他爬上白楊樹,心底里涌起一種幸福感。所有的房屋都在他的屁股下,太陽(yáng)也在他的屁股下。太陽(yáng)落得很快,不圓,像一個(gè)大鴨蛋。他看到遠(yuǎn)遠(yuǎn)近近的草屋上,朽爛的麥秸草被雨水抽打得平平的,留著一層夏天生長(zhǎng)的青苔,青苔上落滿斑斑點(diǎn)點(diǎn)的雀屎c街上塵土很厚,一輛綠色的汽車駛過(guò)去,攪起一股沖天的灰土,好久才消散。灰塵散后,他看到有一條被汽車輪子碾出了腸子的黃色小狗蹣跚在街上,狗腸子在塵土中拖著,像一條長(zhǎng)長(zhǎng)的繩索,小狗一聲也不叫,心平氣和地走著,狗毛上泛起的溫暖漸漸遠(yuǎn)去,黃狗走成黃兔,走成黃鼠,終于走得不見蹤影。四處如有空瓶的鳴聲,遠(yuǎn)近不定,人世的冷暖都一塊塊涂在物上,樹上半冷半熱,他如抱葉的寒蟬一樣觳觫著,見一粒鳥糞直奔房瓦而去。女孩又在下邊喊他,他沒(méi)有聽。他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看著瓦房前的院子,他要不是爬上白楊樹,是永遠(yuǎn)也看不到這個(gè)院子的,盡管樹下這個(gè)眼睛烏黑的小女孩經(jīng)常找他玩,但爹娘卻反復(fù)叮嚀他,不準(zhǔn)去小珍家玩。女孩就是小珍嗎?他很疑惑地問(wèn)著自己。他總是迷迷瞪瞪的,村里人都說(shuō)他少個(gè)心眼。他看著院子,院子里砌著很寬的甬道,有一道影壁墻,墻邊的刺兒梅花葉凋零,只剩下紫紅色的藤條,院里還立著兩輛自行車,車圈上的鍍鎳一閃一閃地刺著他的眼。一個(gè)高大漢子從屋里出來(lái),在墻根下大大咧咧地撒尿,男孩接著看到這個(gè)人紫紅色的臉,嚇得緊貼住樹干,連氣兒都不敢喘。這個(gè)人曾經(jīng)擰著他的耳朵,當(dāng)著許多人的面問(wèn):“小虎,一條狗幾條腿?”他把嘴巴使勁朝一邊咧著,說(shuō):“三條!”眾人便哈哈大笑。他記得當(dāng)時(shí)父親和哥哥也都在人群里,哥哥臉憋得通紅,父親尷尬地陪著眾人笑。哥哥為此揍他,父親拉住哥哥,說(shuō):“書記愿意逗他,說(shuō)明跟咱能合得來(lái),說(shuō)明眼里有咱。”哥哥松開他,拿過(guò)一塊烏黑發(fā)亮的紅薯面餅子杵到他嘴邊,惱怒地問(wèn):“這是什么?”他咬牙切齒地說(shuō):
“狗屎!”
“小虎,你快點(diǎn)呀!”女孩在樹下喊。
他又慢慢地往上爬。這時(shí)他的雙腿哆嗦得很厲害。樹下瓦屋上的煙筒里,突然冒出了白色的濃煙,濃煙一縷縷地從枝條縫隙中,從鴉鵲巢里往上躥。鴉鵲巢中滾動(dòng)著骯臟的羽毛,染著赤色陽(yáng)光的黑鳥圍著他飛動(dòng),噪叫。他用一只手攀住了那根一把粗細(xì)的樹杈,用力往下扳了一下,整棵樹都晃動(dòng)了,樹杈沒(méi)有斷。
“使勁扳,”女孩喊,“樹倒下了,它歪來(lái)歪去原來(lái)是嚇唬人的。”
他用力扳著樹權(quán),樹杈彎曲著,彎曲著,真正像一張弓。他的胳膊麻酥酥的,手指尖兒發(fā)脹。樹杈不肯斷,又猛地彈回去。雙腿抖得更厲害了,腦袋沉重地垂下去。女孩在仰著臉看他。樹下的煙霧像浪花一樣向上翻騰。他渾身發(fā)冷,腦后有兩根頭發(fā)很響地直立了起來(lái),他又一次感到自己爬得是這樣的高。那根直溜溜光滑滑的樹權(quán)還在驕傲地直立著,好像對(duì)他挑戰(zhàn)。他把兩條腿盤起來(lái),伸出兩只手拉住樹杈,用力往下拉,樹杈兒咝咝地叫著,頂梢的細(xì)條和其他細(xì)條碰撞著,噼噼啪啪地響。他把全身的重量和力量都用到樹杈上,雙腿雖然還攀在樹枝干上,但已被忘得干干凈凈。樹杈愈彎曲,他心里愈是充滿仇恨,他低低地吼叫了一聲,騰躍過(guò)去,樹杈斷了。樹權(quán)斷裂時(shí)發(fā)出很脆的響聲,他頭顱里有一根筋愉快地跳動(dòng)了一下,全身沉浸在一種愉悅感里。他的身體輕盈地飛起來(lái),那根很長(zhǎng)的樹權(quán)伴著他飛行,清冽的大氣,白色的炊煙,橙色的霞光,在身體周圍翻來(lái)滾去。匆忙中,他看到從忽然變扁了的瓦房里,跑出了一個(gè)身穿大花襖的女人,她的嘴巴里發(fā)出馬一樣的叫聲。
女孩正眼睜睜地往樹上望著,忽然發(fā)現(xiàn)男孩掛在那根樹權(quán)上,像一顆肥碩的果實(shí)。她猜想他一定非常舒服,她羨慕得要命,也想掛到樹權(quán)上去。但很快就起了變化,男孩伴著樹枝慢悠悠地落下來(lái),她看到他的身體拉得很長(zhǎng),似一匹抖開了的棕綢緞,從樹梢上直掛下來(lái),那根她選中的樹杈抽打著綢緞,索然有聲。她捧著男孩的衣服往前走了一步,猛然覺(jué)得一根柔韌的枝條猛抽著腮幫子,那匹棕色綢緞也落到了身上。她覺(jué)得這匹綢緞像石頭一樣堅(jiān)硬,碰一下都會(huì)發(fā)出敲打鐵皮般的轟鳴。
他莫名其妙地從地上爬起來(lái),身上有個(gè)別部位略感酸麻,其他一切都很好。但他馬上就看到了女孩躺在樹枝下,黑黑的眼睛半睜半閉,一縷藍(lán)色的血順著他的嘴角慢慢地往下流。他跪下去,從樹枝縫里伸進(jìn)手,輕輕地戳了一下女孩的臉。她的臉很硬,像充足了氣的皮球。
穿花襖的女人飛一般來(lái)到房后,罵道:“小壞種,你能上了天?你爹和你娘怎么弄出你這么個(gè)野種來(lái)?折我一根樹杈我掰斷你一根肋條!”
她氣洶洶地沖到跪在地上的男孩面前,踢出的腳剛剛接觸到男孩的脊梁,便無(wú)力地落下了。她的雙眼發(fā)直,嘴巴歪擰著,撲到女孩身上,哭叫著:“小珍子,小珍子,我的孩子,你這是怎么啦……”
……一只渾身虎紋斑駁的貓?zhí)ぶ拥躺系目莶萆狭说添敚鈮|了腳爪踩著枯草,幾乎沒(méi)有聲音。它吃驚地站在男孩面前,雙眼放綠光,嗚嗚地發(fā)著威,尾巴像桅桿一樣直豎起來(lái)。他膽怯地望著它。它不走,聞著從他身上散發(fā)出的濃重的血腥味,他無(wú)法忍受它那兩只磷光閃爍的眼睛的逼視,困難地站立起來(lái)。
月亮已升起很高了,但依然水淋淋的不甚明亮。西半天的星辰射出金剛石一樣的光芒。村子完全被似煙似霧的氣體籠罩了,他不回頭也知道,村里的樹木只有那棵白楊樹能從霧中露出一節(jié)頂梢,像洪水中的樹。想到白楊樹,他鼻子眼里都酸溜溜的。他小心翼翼地繞過(guò)那只威風(fēng)凜凜的野貓,趔趔趄趄地下了河,河里是一片影影綽綽的銀灰色,不是水,是暄騰騰的沙土。已經(jīng)連續(xù)三年大旱,河里垛著干燥的柴草,貓?jiān)诒澈鬀_著他叫,但他已無(wú)心去理它了。他的赤腳踩著熱乎乎的沙土,一步一個(gè)腳印。沙土的熱從腳心一寸寸地上行,先是很粗很盛,最后僅僅如一條蛛絲,好像沿著骨髓,一直鉆到腦袋里。他搞不清自己的`身體在哪兒,整個(gè)人變成了模模糊糊的一團(tuán),像個(gè)捉摸不定的暗影,到處都是熱熱辣辣的感覺(jué)。
他摔倒在沙窩里時(shí),月亮顫抖不止,把血水一樣的微光淋在他赤裸的背上。他趴著,無(wú)力再動(dòng),感覺(jué)到月光像熱烙鐵一樣燙著背,鼻子里充溢著燒豬皮的味道。
大花襖女人并沒(méi)有打他,她只顧哭她的心肝肉兒去了。他聽著女人驚險(xiǎn)的哭聲,毛骨悚然,他知道自己犯下了。他看到高大的紅臉漢子躥了過(guò)來(lái),耳朵里嗡了一聲,接著便風(fēng)平浪靜。他好像被扣在一個(gè)穹隆般的玻璃罩里,一群群的人隔著玻璃跑動(dòng)著,急匆匆,亂哄哄,一窩蜂,如救火,如沖鋒,張著嘴喊叫卻聽不到聲。他看到兩條粗壯的腿在移動(dòng),兩只磨得發(fā)了光的翻毛皮鞋直對(duì)著他的胸口來(lái)了。接著他聽到自己肚子里有只青蛙叫了一聲,身體又一次輕盈地飛了起來(lái),一股甜腥的液體涌到喉嚨。他只哭了一聲,馬上就想到了那條在大街上的塵土中拖著腸子行進(jìn)的黃色小狗。小狗為什么一聲不叫呢?他反反復(fù)復(fù)地想著。翻毛皮鞋不斷地使他翻斤斗。他恍然覺(jué)得自己的腸子也像那條小狗一樣拖出來(lái)了,腸子上沾滿了金黃色的泥土。那根他費(fèi)了很大力量才扳下來(lái)的白楊樹權(quán)也飛動(dòng)起來(lái)了,柔韌如皮條的枝條狂風(fēng)一樣呼嘯著,枝條一截截地飛濺著,一股清新的楊樹漿汁的味道在他唇邊漾開去,他起初還在地上翻滾著,后來(lái)就嘴啃著泥土,一動(dòng)也不動(dòng)了。
沙土漸漸地涼下來(lái)了,他身上的溫度與沙土一起降著。他面朝下趴著,細(xì)小的沙塵不斷被吸到鼻孔里去。他很想動(dòng)一下,但不知身體在哪兒,他努力思索著四肢的位置,終于首先想到了胳膊。他用力把胳膊撐起來(lái),脖子似乎折斷了,頸椎骨在咯嘣著響。他沉重地再次趴下,滿嘴里都是沙土,舌頭僵硬得不能打彎。連吃了三口沙土后,他終于翻了一個(gè)身。這時(shí),他非常辛酸地仰望著夜空,月亮已經(jīng)在正南方,而且褪盡了血色,變得明晃晃的,晦暗的天空也成了漂漂亮亮的銀灰色,河沙里有黃金般的光輝在閃耀,那光輝很冷,從四面八方包圍著他,像小刀子一樣刺著他。他求援地盯著孤獨(dú)的月亮。月亮照著他,月亮臉色蒼白,月亮里的暗影異常清晰。他還從來(lái)沒(méi)有這樣認(rèn)真地看過(guò)月亮,月亮里的暗影使他驚訝極了。他感到它非常陌生,閉上眼睛就忘了它的模樣。他用力想著月亮,父親的臉從蒼白的月亮中顯出來(lái)了。
他今天才知道父親的模樣。父親有兩只腫眼睛,眼珠子像浸泡在鹽水里的地梨。父親跪在地上也很高。翻毛皮鞋也許踢過(guò)父親,也許沒(méi)踢。父親跪著哀求:“書記,您大人不見小人的怪,這個(gè)狗崽子,我一定狠揍。他十條狗命也不值小珍子一條命,只要小珍子平安無(wú)事,要我身上的肉我也割……”書記對(duì)著父親笑。書記眼里噴著一圈圈藍(lán)煙。
哥哥拖著他往家走。他的腳后跟劃著堅(jiān)硬的地面。走了很久,還沒(méi)有走出白楊樹的影子。鴉鵲飛掠而過(guò)的陰影像絨毛一樣掃著他的臉。
哥哥把他扔在院子里,對(duì)準(zhǔn)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腳,喊道:“起來(lái)!你專門給家里闖禍!”他躺在地上不肯動(dòng),哥哥很有力地連續(xù)踢著他的屁股,說(shuō):“滾起來(lái)!你作了孽還有了功啦是不?”
他奇跡般地站了起來(lái),一步步倒退到墻角下去,站定后,驚恐地看著瘦長(zhǎng)的哥哥。
哥哥憤怒地對(duì)母親說(shuō):“砸死他算了,留著也是個(gè)禍害。本來(lái)我今年還有希望去當(dāng)個(gè)兵,這下子全完了。”
他悲哀地看著母親,母親從來(lái)沒(méi)有打過(guò)他。母親流著淚走過(guò)來(lái),他委屈地叫了一聲娘,眼淚鼻涕一齊流了出來(lái)。
母親卻兇狠地罵:“鱉蛋!你還哭?還挺冤?打死你也不解限!”
母親戴著銅頂針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門子上。他干嚎了一聲。不像人能發(fā)出的聲音使母親愣了一下,她彎腰從草垛上抽出一根干棉花柴,對(duì)著他沒(méi)鼻子沒(méi)眼地抽著,棉花柴嘩啷嘩啷地響著,嚇得墻頭上的麻雀像子彈一樣射進(jìn)暮色里去。他把身體使勁倚在墻下,看著棉花柴在眼前劃出的紅色弧線……
村子里一聲瘦弱的雞鳴,把他從迷蒙中喚醒。他的肚子好像凝成一個(gè)冰坨子,周身都冷透了,月亮偏到西邊去了,天河里布滿了房瓦般的浪塊。他想翻身,居然很輕松地翻了一個(gè)身,身體像根圓木一樣滾動(dòng)著。他當(dāng)然不知道他正在滾下一個(gè)小斜坡,斜坡下有一個(gè)可憐巴巴的紅薯蔓垛。紫勾勾的薯蔓發(fā)著淡淡的苦澀味兒,一群群棗核大的螢火蟲在薯蔓上爬著,在他眼睛里和耳朵里飛著。父親搖搖晃晃地來(lái)了,母親舉著那棵打成光桿的棉花柴,慢慢地退到一邊去。
“滾起來(lái)!”父親怒吼一聲。他把身體用力往后縮著。
他把身體用力往后縮著,紅薯蔓刷拉拉響著。月亮遍地,河里凝結(jié)著一層冰霜,一個(gè)個(gè)草垛如同碉堡,凌亂擺布在河上。甜腥的液體又沖在喉頭,他不由自主地大張開嘴巴,把一個(gè)個(gè)面疙瘩一樣的凝塊吐出來(lái)。吐出來(lái)的凝塊擺在嘴邊,像他曾經(jīng)見過(guò)的貓屎。他怕極了,一種隱隱約約的預(yù)感出現(xiàn)了。
那是一個(gè)眉毛細(xì)長(zhǎng)的媳婦,她躺在一張葦席上,臉如紫色花瓣。旁邊有幾個(gè)人像唱歌一樣哭著。這個(gè)小媳婦真好看,活著像花,死去更像花。他是跟著一群人擠進(jìn)去看熱鬧的,那是一間空屋,一根紅色的褲腰帶還掛在房梁上。死者的臉平靜安詳,把所有的人都不放進(jìn)眼里。大隊(duì)里的紅臉膛的支部書記眼淚汪汪地來(lái)看望死者,眾人迅速地為他讓開道路。支部書記站在小媳婦尸身前,眼淚盈眶,小媳婦臉上突然綻開了明媚的微笑。眉毛如同燕尾一樣剪動(dòng)著。支部書記一下子化在地上,渾身上下都流出了透明的液體。人們都說(shuō)小媳婦死得太可惜啦。活著默默無(wú)聞的人,死后竟能引起這么多人的注意,連支部書記都來(lái)了,可見死不是件壞事。他當(dāng)時(shí)就覺(jué)得死是件很誘人的事情。隨著雜亂的人群走出空屋,他很快就把小媳婦,把死,忘了。現(xiàn)在,小媳婦,死,依稀還有那條黃色小狗,都沿著遍布銀輝的河底,無(wú)怨無(wú)怒地對(duì)著他來(lái)了。他已經(jīng)聽到了她們的雜沓的腳步聲,看到了她們的黑色的巨大翅膀。
在看到翅膀之后,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來(lái)龍去脈,他看到自己踏著冰冷的霜花,在河水中走來(lái)又走去,一群群的鰻魚像粉條一樣在水中滑來(lái)滑去。他用力擠開鰻魚,落在一間黑釉亮堂堂的房子里。小北風(fēng)從鼠洞里、煙筒里、墻縫里不客氣地刮進(jìn)來(lái)。他憤怒地看著這個(gè)金色的世界,寒冬里的陽(yáng)光透過(guò)窗紙射進(jìn)來(lái),照耀著炕上的一堆細(xì)沙土。他濕漉漉地落在沙土上,身上滾滿了細(xì)沙。他努力哭著,為了人世的寒冷。父親說(shuō):“嚎,嚎,一生下來(lái)就窮嚎!”聽了父親的話,他更感到徹骨的寒冷,身體像吐絲的蠶一樣,越縮越小,布滿了皺紋。
昨天下午那個(gè)時(shí)刻,他發(fā)著抖倚在自家的土墻上,看著父親一步步走上來(lái)。夕陽(yáng)照著父親高大的身軀,照著父親愁苦的面孔。他看到父親一腳赤裸,一腳穿鞋,一腳高一腳低地走過(guò)來(lái)。父親左手提著一只鞋子,右手拎著他的脖子,輕輕提起來(lái),用力一摔。他第三次感到自己在空中飛行。他暈頭轉(zhuǎn)向地爬起來(lái),發(fā)現(xiàn)父親身體更加高大,長(zhǎng)長(zhǎng)的影子鋪滿了整個(gè)院子。父親和哥哥像用紙殼剪成的紙人,在血紅的夕陽(yáng)中抖動(dòng)著。母親那只厚底老鞋第一下打在他的腦袋上,把他的脖子幾乎釘進(jìn)腔子里去。那只老鞋更多的是落在他的背上,急一陣,慢一陣,鞋底越來(lái)越薄,一片片泥土飛散著。
“打死你也不解恨!雜種。真是無(wú)冤無(wú)仇不結(jié)父子。”父親悲哀地說(shuō)著。說(shuō)話時(shí)手也不停,打薄了的鞋底子與他的黏糊糊的脊背接觸著,發(fā)出越來(lái)越響亮的聲音。他憤怒得不可忍受,心臟像鐵砣子一樣僵硬。他產(chǎn)生了一種說(shuō)話的欲望,這欲望隨著父親的敲擊,變得愈加強(qiáng)烈,他聽到自己聲嘶力竭地喊道:“狗屎!”
父親怔住了,鞋子無(wú)聲地落在地上。他看到父親滿眼都是綠色的眼淚,脖子上的血管像綠蟲子一樣蠕動(dòng)著。他咬牙切齒地對(duì)著父親又喊叫:“臭狗屎!”父親低沉地嗚嚕了一聲,從房檐下摘下一根僵硬的麻繩子,放進(jìn)咸菜缸里的鹽水里泡了泡,小心翼翼地提出來(lái),胳膊撐開去,繩子淅淅瀝瀝地滴著濁水。“把他的褲子剝下來(lái)!”父親對(duì)著哥哥說(shuō)。哥哥渾身顫抖著,從一大道蒼黃的陽(yáng)光中游了過(guò)來(lái)。在他面前,哥哥站定,不敢看他的眼睛卻看著父親的眼睛,喃喃地說(shuō):“爹,還是不剝吧……”父親果斷地一揮手,說(shuō):“剝,別打破褲子。”哥哥的目光迅速地掠過(guò)他凝固了的臉和魚刺般的胸脯,直直地盯著他那條褲頭。哥哥彎下腰。他覺(jué)得大腿間一陣冰冷,褲頭像云朵樣落下去,墊在了腳底下。哥哥捏住他的左腳脖子,把褲頭的一半扯出來(lái),又捏住他的右腳脖子,把整個(gè)褲頭扯走。他感到自己的一層皮被剝走了,望著哥哥畏畏縮縮地倒退著的影子,他又一次高喊:“臭狗屎!”
父親揮起繩子。繩子在空中彎彎曲曲地飛舞著,接近他屁股時(shí),則猛然繃直,同時(shí)發(fā)出清脆的響聲。他哼了一聲,那句罵慣了的話又從牙縫里擠出來(lái)。父親連續(xù)抽了他四十繩子,他連叫四十句。最后一下,繩子落在他的屁股上時(shí),沒(méi)有繃直,彎彎曲曲,有氣無(wú)力;他的叫聲也彎彎曲曲,有氣無(wú)力,很像痛苦的呻吟。父親把變了色的繩子扔在地上,氣喘吁吁地進(jìn)了屋。母親和哥哥也進(jìn)了屋。母親惱怒地對(duì)父親說(shuō):“你把我也打死算了,我也不想活了。你把俺娘們?nèi)蛩浪懔耍钪€趕不上死去利索。都是你那個(gè)老糊涂的爹,明知道共產(chǎn)黨要來(lái)了,還去買了二十畝兔子不拉屎的澇洼地。劃成一個(gè)上中農(nóng),一輩兩輩三輩子啦,都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活著。”哥哥說(shuō):“那你當(dāng)初為什么要嫁給老中農(nóng)?有多少貧下中農(nóng)你不能嫁?”母親放聲慟哭起來(lái),父親也“唁唁瞎哈,唁瞎唁哈”地哭起來(lái),在父母的哭聲中,那條繩子像蚯蚓一樣扭動(dòng)著,一會(huì)兒扭成麻花,一會(huì)兒卷成螺旋圈,他猛一乍汗毛,肌肉縮成塊塊條條,借著這股勁,他站起來(lái),在暮色蒼茫的院子里沉思了幾秒鐘,便跳躍著奔向柴門,從縫隙中鉆了出來(lái)……天亮前,他又一次醒過(guò)來(lái),他已沒(méi)有力量把頭抬起來(lái),看看蒼白的月亮,看看蒼白的河道。河堤上響著母親的慘叫聲:虎——虎一一虎——虎兒啦啦啦啦——我的苦命的孩呀呀呀呀……。這叫聲刺得他尚有知覺(jué)的地方發(fā)痛發(fā)癢,他心里充滿了報(bào)仇雪恨后的歡娛。他竭盡全力喊了一一聲,胸口一陣灼熱,有干燥的紙片破裂聲在他的感覺(jué)中響了一聲,緊接著是難以忍受的寒冷襲來(lái)。他甚至聽到自己落進(jìn)冰窟窿里的響聲,半凝固的冰水僅僅濺起七八塊冰屑,便把他給固定住了。
鮮紅太陽(yáng)即將升起那一剎那,他被一陣沉重野蠻的歌聲吵醒了。這歌聲如太古森林中呼嘯的狂風(fēng),挾帶著枯枝敗葉污泥濁水從干涸的河道中滾滾而過(guò)。狂風(fēng)過(guò)后,是一陣古怪的、緊張的沉默。在這沉默中,太陽(yáng)冉冉出山,砉然奏起溫暖的音樂(lè),音樂(lè)撫摸著他傷痕斑斑的屁股,引燃他腦袋里的火苗,黃黃的,紅紅的,終于變綠變小,明明暗暗跳動(dòng)幾下,熄滅。
人們找到他時(shí),他已經(jīng)死了……他的父母目光呆滯,猶如魚類的眼睛……百姓們面如荒涼的沙漠,看著他布滿陽(yáng)光的屁股……好像看著一張明媚的面孔,好像看著我自己……
莫言《枯河》節(jié)選
引導(dǎo)語(yǔ):莫言的小說(shuō)《枯河》運(yùn)用了“象征”的手法和“時(shí)空交叉”的獨(dú)特?cái)⑹陆Y(jié)構(gòu),許多獨(dú)特的意象值得我們思索和探究,這有助于我們理解莫言作品的創(chuàng)作特色和深刻的精神內(nèi)涵。
莫言《枯河》節(jié)選
一輪巨大的水淋淋的鮮紅月亮從村莊東邊暮色蒼茫的原野上升起來(lái)時(shí),村子里彌漫的煙霧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種凄艷的紅色。這時(shí)太陽(yáng)剛剛落下來(lái),地平線下還殘留著一大道長(zhǎng)長(zhǎng)的紫云。幾顆瘦小的星斗在日月之間暫時(shí)地放出蒼白的光芒。村子里朦朧著一種神秘的氣氛,狗不叫,貓不叫,鵝鴨全是啞巴。月亮升著,太陽(yáng)落著,星光熄滅著的時(shí)候,一個(gè)孩子從一扇半掩的柴門中鉆出來(lái),一鉆出柴門,他立刻化成一個(gè)幽靈般的灰影子,輕輕地漂浮起來(lái)。他沿著村后的河堤舒緩地漂動(dòng)著,河堤下枯萎的衰草和焦黃的楊柳落葉喘息般地響著。他走得很慢,在枯草折腰枯葉破裂的細(xì)微聲響中,一跳一跳地上了河堤。在河堤上,他蹲下來(lái),籠罩著他的陰影比他的形體大得多。直到明天早晨他像只青蛙一樣蜷伏在河底的紅薯蔓中長(zhǎng)眠不醒時(shí),村里的人們圍成團(tuán)看著他,多數(shù)人不知道他的歲數(shù),少數(shù)人知道他的名字。而那時(shí),他的父母全都目光呆滯,猶如魚類的眼睛,無(wú)法準(zhǔn)確地回答鄉(xiāng)親們提出的關(guān)于孩子的問(wèn)題。他是個(gè)黑黑瘦瘦,嘴巴很大,鼻梁短促,目光彈性豐富的從來(lái)不知道什么叫生病的男孩子。他攀樹的技能高超。明天早晨,他要用屁股迎著初升的太陽(yáng),臉深深地埋在烏黑的瓜秧里。一群百姓面如荒涼的沙漠,看著他的比身體其他部位的顏色略微淺一些的屁股。這個(gè)屁股上布滿傷痕,也布滿陽(yáng)光,百姓們看著它,好像看著一張明媚的面孔,好像看著我自己。
他蹲在河堤上,把雙手夾在兩個(gè)腿彎子里,下巴放在尖削的膝蓋上。他感到自己的心像只水耗子一樣在身體內(nèi)哧溜哧溜地跑著,有時(shí)在喉嚨里,有時(shí)在肚子里,有時(shí)又跑到四肢上去,體內(nèi)仿佛有四通八達(dá)的鼠洞,像耗子一樣的心臟,可以隨便又輕松地滑動(dòng)。月亮持續(xù)上升,依然水淋淋的,村莊里向外膨脹著非煙非霧的氣體,氣體一直上升,把所有的房屋罩進(jìn)下邊,村中央那棵高大的白楊樹把頂梢插進(jìn)迷蒙的氣體里,挺拔的樹干如同傘柄,氣體如傘如笠,也如華蓋如毒蘑菇。村莊里的所有樹木都瑟縮著,不敢超過(guò)白楊樹的高度,白楊樹驕傲地向天里鉆,離地二十米高的枝丫間,有一團(tuán)亂糟糟的柴棍,柴棍間雜居著喜鵲和烏鴉,它們每天都爭(zhēng)吵不休,如果月光明亮,它們會(huì)跟著月亮噪叫。
或許,他在一團(tuán)陰影的包圍中蹲在河堤上時(shí),曾經(jīng)有抽泣般的聲音從他干渴的喉嚨里冒出來(lái),他也許是在回憶剛剛過(guò)去的事情。那時(shí)候,他穿著一件肥大的褂子,赤著腳,站在白楊樹下。白楊樹前是五間全村唯一的瓦房,瓦房里的孩子是一個(gè)很漂亮的小女孩,漆黑的眼睛像兩粒黑棋子。女孩子對(duì)他說(shuō):“小虎,你能爬上這棵白楊樹嗎?”
他怔怔地看著女孩,嘴巴咧了咧,短促的鼻子上布滿皺紋。
“你爬不上去,我敢說(shuō)你爬不上去!”
他用牙齒咬住了厚厚的嘴唇。
“你能上樹給我折根樹杈嗎?就要那根,看到了沒(méi)有?那根直溜的,我要用它削一管槍,削好了咱倆一塊耍,你演特務(wù),我演解放軍。”
他用力搖搖頭。
“我知道你上不去,你不是小虎,是只小老母豬!”女孩憤憤地說(shuō),“往后我不跟你耍了。”
他用黑眼睛很亮地看著女孩,嘴咧著,像是要哭的樣子。他把腳放在地上搓著,終于干巴巴地說(shuō):“我能上去。”
“你真能?”女孩驚喜地問(wèn)。
他使勁點(diǎn)點(diǎn)頭,把大褂子脫下來(lái),露出青色的肚皮。他說(shuō):“你給我望著人,俺家里的人不準(zhǔn)我上樹。”
女孩接過(guò)衣裳,忠實(shí)地點(diǎn)了點(diǎn)頭。
他雙腳抱住樹干。他的腳上生著一層很厚的胼胝,在銀灰色的樹干上把得牢牢的,一點(diǎn)都不打滑。他爬起樹來(lái)像一只貓,動(dòng)作敏捷自如,帶著一種天生的素質(zhì)。女孩抱著他的衣服,仰著臉,看著白楊樹慢慢地傾斜,慢慢地對(duì)著自己倒過(guò)來(lái)。恍惚中,她又看到光背赤腳的男孩把粗大的白楊樹干墜得像弓一樣彎曲著,白楊樹好像隨時(shí)都會(huì)把他彈射出去。女孩在樹下一陣陣發(fā)顫。后來(lái),她看到白楊樹又倏忽挺直。在漸漸西斜的深秋陽(yáng)光里,白花花的楊樹枝聚攏上指,瑟瑟地彈撥著淺藍(lán)色的空氣。冰一樣澄澈的天空中,一綹綹的細(xì)密楊枝飛舞著;殘存在枝梢上的個(gè)把楊葉,似乎已經(jīng)枯萎,但暗藍(lán)的顏色依舊不褪;隨著枝條的擺動(dòng),枯葉在窸窣作響。白楊樹奇妙的動(dòng)作撩亂了女孩的眼睛,她看到越爬越高的男孩的黑色般的脊梁上,閃爍著鴉翅般的光翚。
“你快下來(lái),小虎,樹要倒了!”女孩對(duì)著樹上的男孩喊起來(lái)。男孩已經(jīng)爬進(jìn)稀疏的白楊樹冠里去了,樹枝間有鴉鵲穿梭飛動(dòng),像一群碩大的蜜蜂,像一群陰郁的蝴蝶。
“樹要斷啦!”女孩的喊聲像火苗子一樣燒著他的屁股,他更快地往上爬。鴉鵲翅膀扇起的腥風(fēng)直吹到他的脖頸子里,使他感到脊梁溝里一陣陣發(fā)涼。女孩的喊叫提醒了他,他也覺(jué)得樹干纖細(xì)柔弱,彎曲得非常厲害,冰塊一樣的天空在傾斜著旋轉(zhuǎn)。他的腿上有一塊肉突突地跳起來(lái),他低頭看著這塊跳動(dòng)的肌肉,看得清清楚楚。就在這時(shí)候,他又聽到了女孩的叫聲,女孩說(shuō):“小虎,你下來(lái)吧,樹歪倒了,樹就要歪到俺家的瓦屋上去了,砸碎俺家的瓦,俺娘要揍你的!”他打了一個(gè)愣怔,把身體貼在樹干上,低眼往下看。這時(shí)他猛然一陣頭暈眼花,他驚異地發(fā)現(xiàn)自己爬得這樣高。白楊樹把全村的樹都給蓋住了,猶如鶴立雞群。他爬上白楊樹,心底里涌起一種幸福感。所有的房屋都在他的`屁股下,太陽(yáng)也在他的屁股下。太陽(yáng)落得很快,不圓,像一個(gè)大鴨蛋。他看到遠(yuǎn)遠(yuǎn)近近的草屋上,朽爛的麥秸草被雨水抽打得平平的,留著一層夏天生長(zhǎng)的青苔,青苔上落滿斑斑點(diǎn)點(diǎn)的雀屎。街上塵土很厚,一輛綠色的汽車駛過(guò)去,攪起一股沖天的灰土,好久才消散。灰塵散后,他看到有一條被汽車輪子碾出了腸子的黃色小狗蹣跚在街上,狗腸子在塵土中拖著,像一條長(zhǎng)長(zhǎng)的繩索,小狗一聲也不叫,心平氣和地走著,狗毛上泛起的溫暖漸漸遠(yuǎn)去,黃狗走成黃兔,走成黃鼠,終于走得不見蹤影。四處如有空瓶的鳴聲,遠(yuǎn)近不定,人世的冷暖都一塊塊涂在物上,樹上半冷半熱,他如抱葉的寒蟬一樣觳觫著,見一粒鳥糞直奔房瓦而去。女孩又在下邊喊他,他沒(méi)有聽。他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看著瓦房前的院子,他要不是爬上白楊樹,是永遠(yuǎn)也看不到這個(gè)院子的,盡管樹下這個(gè)眼睛烏黑的小女孩經(jīng)常找他玩,但爹娘卻反復(fù)叮嚀他,不準(zhǔn)去小珍家玩。女孩就是小珍嗎?他很疑惑地問(wèn)著自己。他總是迷迷瞪瞪的,村里人都說(shuō)他少個(gè)心眼。他看著院子,院子里砌著很寬的甬道,有一道影壁墻,墻邊的刺兒梅花葉凋零,只剩下紫紅色的藤條,院里還立著兩輛自行車,車圈上的鍍鎳一閃一閃地刺著他的眼。一個(gè)高大漢子從屋里出來(lái),在墻根下大大咧咧地撒尿,男孩接著看到這個(gè)人紫紅色的臉,嚇得緊貼住樹干,連氣兒都不敢喘。這個(gè)人曾經(jīng)擰著他的耳朵,當(dāng)著許多人的面問(wèn):“小虎,一條狗幾條腿?”他把嘴巴使勁朝一邊咧著,說(shuō):“三條!”眾人便哈哈大笑。他記得當(dāng)時(shí)父親和哥哥也都在人群里,哥哥臉憋得通紅,父親尷尬地陪著眾人笑。哥哥為此揍他,父親拉住哥哥,說(shuō):“書記愿意逗他,說(shuō)明跟咱能合得來(lái),說(shuō)明眼里有咱。”哥哥松開他,拿過(guò)一塊烏黑發(fā)亮的紅薯面餅子杵到他嘴邊,惱怒地問(wèn):“這是什么? ”他咬牙切齒地說(shuō):
“狗屎!”
“小虎,你快點(diǎn)呀!”女孩在樹下喊。
他又慢慢地往上爬。這時(shí)他的雙腿哆嗦得很厲害。樹下瓦屋上的煙筒里,突然冒出了白色的濃煙,濃煙一縷縷地從枝條縫隙中,從鴉鵲巢里往上躥。鴉鵲巢中滾動(dòng)著骯臟的羽毛,染著赤色陽(yáng)光的黑鳥圍著他飛動(dòng),噪叫。他用一只手攀住了那根一把粗細(xì)的樹杈,用力往下扳了一下,整棵樹都晃動(dòng)了,樹杈沒(méi)有斷。
莫言作品《秋水》
我爺爺八十八歲那年春天一個(gè)天氣晴朗的上午,村里人都見他坐著大馬扎子倚在我家臨街的菜園子墻上閉目養(yǎng)神。天晌午,母親讓我去叫爺爺回家吃飯。我跑到他身邊,大聲喊叫也不見應(yīng),用手推去,才發(fā)現(xiàn)他已不會(huì)動(dòng)。飛快報(bào)告家里人,一齊涌出來(lái),圍上去,推拿呼叫,也終究不濟(jì)事。爺爺死得非常體面,面色紅潤(rùn),栩栩如生,令人敬仰不止。村里人紛紛說(shuō)我爺爺生前積下善功,才得這等仙死。我們?nèi)叶紴闋敔數(shù)乃栏械綐s耀。
據(jù)說(shuō),爺爺年輕時(shí),殺死三個(gè)人,放起一把火,拐著一個(gè)姑娘,從河北保定府逃到這里,成了高密東北鄉(xiāng)最早的開拓者。那時(shí)候,高密東北鄉(xiāng)還是蠻荒之地,方圓數(shù)十里,一片大澇洼,荒草沒(méi)膝,水汪子相連,棕兔子紅狐貍,斑鴨子白鷺鷥,還有諸多不識(shí)名的動(dòng)物棄斥洼地,尋常難有人來(lái)。我爺爺帶著那姑娘來(lái)了。
那個(gè)姑娘很自然地就成了我的奶奶。他們是春天跑到這里來(lái)的,在草窩子里滾過(guò)幾天后,我奶奶從頭上拔下金釵,腕上褪下玉鐲,讓爺爺拿到老遠(yuǎn)的地方賣了,換來(lái)農(nóng)具和日用家具,到洼子中央一座莫名其妙的小土山上搭了一個(gè)窩棚。從此后就爺爺開荒,奶奶捕魚,把一個(gè)大澇洼子的平靜攪碎了。消息慢慢傳出去,神話般談?wù)撝鬂惩堇镉幸粚?duì)年輕夫妻,男的黑,魁梧,女的白,標(biāo)致,還有一個(gè)不白不黑的小子……陸續(xù)便有匪種寇族遷來(lái),設(shè)莊立屯,自成一方世界——這是后話。
我懂人事時(shí),那座莫名其妙的小土山已被十八鄉(xiāng)的貧下中農(nóng)搬走了,洼地似乎長(zhǎng)高,天雨日少,很難見到水,隔五六里就是一個(gè)村子。聽爺爺輩的老人講起這里的過(guò)去,從地理環(huán)境到奇聞?shì)W事,總感到橫生出鬼雨神風(fēng),星星點(diǎn)點(diǎn)如磷火閃爍,不知真耶?假耶?
……我爺爺和我奶奶開荒地種五谷,捕魚蝦獵狐兔,起初還有些提心吊膽,夢(mèng)里常憶起那幾顆血淋淋的人頭,日子一多,便淡忘了。我爺爺說(shuō),大洼里無(wú)兵無(wú)官,天高皇帝遠(yuǎn),就是蚊蟲多得要命。陰雨天前,常常可見到一團(tuán)團(tuán)黑煙壓著草梢和水面飛翔,伸手過(guò)去,能抓下一小把。為避蚊蟲,爺爺和奶奶有時(shí)跳進(jìn)水里去,只露出兩個(gè)鼻孔出氣。爺爺還說(shuō),潮濕的草中,每到晚間就放出幽幽綠光,連成一片,好像水在流動(dòng)。泥沼里的螃蟹總是趁著磷光覓食,天明你去淤泥上看,密密麻麻全是蟹爪印。這些蟹子,長(zhǎng)成了都如馬蹄大。我甭說(shuō)吃,連見也沒(méi)見過(guò)這些大蟹。聽爺爺講過(guò)去的大澇洼子,令人神往神壯,悔不早生六十年。
夏去秋來(lái),爺爺種的高梁曬紅了米,谷子垂下了頭,玉米干了纓,一個(gè)好年景綁到了手上。我父親也在我奶奶腹中長(zhǎng)得全毛全翅,就等著好日子飛出來(lái)闖蕩世界。臨收獲前幾天,突然燠熱起來(lái),花花綠綠的云罩在大澇洼子上,云團(tuán)像炸群的牲口一樣胡亂竄,水洼子里映出一團(tuán)團(tuán)匆匆移動(dòng)的暗影。大雨滂沱,旬日不絕,整個(gè)澇洼子都被雨泡漲了,羅羅索索的雨聲,猶猶豫豫的白霧,晝夜不絕不散。爺爺急躁得罵天罵地。奶奶一陣陣腹痛。奶奶對(duì)爺爺說(shuō):“我怕是要生了。”爺爺說(shuō):“生就生吧。這熊攮的天氣,我恨不得捅它個(gè)窟窿。”爺爺正罵著,就見那太陽(yáng)從云縫中鉆出來(lái),初時(shí)略有些朦朧,立即就射出兩三束極強(qiáng)的白光,掃出了幾道白天。爺爺跑出窩棚,興奮地看著天,聽澇洼里的雨聲漸漸稀少起來(lái),空中尚有少許銀亮雨絲斜著飛。大洼子里積水成片,黃草綠草在水中疲勞地擎著頭。雨聲斷絕,大洼子里一陣陣沉重的風(fēng)響。我爺爺高高地望著他的莊稼,見高梁玉米尚好,臉上有了喜色。隨著風(fēng)響,無(wú)數(shù)的青蛙一齊嗚叫起來(lái),整個(gè)洼子都在哆嗦。爺爺走進(jìn)窩棚,跟奶奶說(shuō)云開日出的事,奶奶說(shuō)她肚子痛得一陣急似一陣,心里害怕。爺爺勸她:“怕什么?瓜熟蒂落。”正說(shuō)著話,聽到四野里響起一陣怪聲,隆隆如滾雷,把蛙鳴聲擠到中間來(lái)。爺爺鉆出棚去,見有黃色的浪涌如馬頭高,從四面撲過(guò)來(lái),浪頭一路響著,齊齊地觸上了土山,洼子里頓時(shí)水深數(shù)米。青蛙好像全給灌死了。荒草沒(méi)了頂,只有爺爺?shù)母吡汉陀衩走€沒(méi)被淹沒(méi)。又一會(huì)兒工夫,玉米和高梁也沒(méi)了頂,八方望出去,滿眼都是黃黃的水,再也見不到別的什么。爺爺長(zhǎng)嘆一聲,鉆進(jìn)棚里。奶奶裸著身子,在草鋪上呼呼叫叫,頭發(fā)上滾滿了草屑,白臉上透出灰色。“洪水漫上來(lái)了!”爺爺憂心忡忡地說(shuō)。奶奶于是不再叫,爬起來(lái),挪出棚子望望,立即鉆進(jìn)來(lái),臉上失了色,五官有些挪位。半晌沒(méi)說(shuō)話,一張嘴,先放出兩根哭聲:“噢——噢——完了,老三,咱活不出去了。”爺爺扶她躺在鋪上,說(shuō):“你是怎么啦?咱人也殺了,火也放了,還有什么好怕的?當(dāng)初就說(shuō),能在一起過(guò)一天,死了也情愿。咱在一起過(guò)了多少個(gè)一天啦?水大沒(méi)不了山,樹高戳不破天,好好生你的孩子,我去看看水。”
我爺爺折了一根樹枝,斜著往下走了幾十步,把樹枝插在亂伸舌頭的水邊上,又返回土山高頂看水。迎著陽(yáng)光的一面只能望出去幾箭遠(yuǎn),便被水面泛起的耀眼的光芒擋住了;背光的一面,卻可以望到眼的盡頭。眼中全是濁污的黃水,不知從哪兒來(lái),不知往哪兒去,一股一股的,撞上了土山,扭在一起,弄出一些大大小小的黑旋渦,時(shí)時(shí)可見一兩只笨拙的蛤蟆直奔旋渦而去,進(jìn)去了,就再也見不到出來(lái)。我爺爺插的那根樹枝又被淹沒(méi)了,這說(shuō)明水還在急漲。望著這浩浩蕩蕩的世界,我爺爺也有些惶然。一會(huì)兒心里空隙極大,像一片寂寞的荒原;一會(huì)兒又滿登登的,五臟六腑仿佛凝成一團(tuán)。發(fā)著愣怔的工夫,水又漲了幾寸,小土山越來(lái)越小,對(duì)比著一看,爺爺心里冷了。他仰天長(zhǎng)嘆一聲,見著瓦藍(lán)的天從云縫中大塊大塊地露出來(lái),掛色的破云被流風(fēng)驅(qū)趕著匆匆奔命。爺爺又在水邊上插了一根樹枝,松弛著臉回了窩棚,對(duì)雙腿亂撲騰的奶奶說(shuō):“你能給我生個(gè)兒子嗎?”
傍晚時(shí),爺爺又出棚看水。一天彩云照著水,紅的紅,黃的黃,云彩模糊地在渾水中漂。水位停在原來(lái)的地方,爺爺頓時(shí)松了心。這時(shí),繞著小山周圍的水面上,忽閃忽閃飛舞著成群結(jié)隊(duì)的銀灰色大鳥。爺爺不認(rèn)識(shí)這種鳥。鳥的鳴叫聲刁鉆古怪,翅羽上涂著霞光。爺爺看到它們從水中銜上一條條白色的魚,便感到肚里有些空,走進(jìn)窩棚去升火做飯。奶奶滿臉是汗,但也沒(méi)忘了問(wèn)水勢(shì)。爺爺說(shuō)水位開始下跌,讓她安心生孩子。奶奶立即哭了,說(shuō):“老三,我年紀(jì)大了,骨縫閉了,怕是生不下這個(gè)孩子來(lái)啦。”爺爺說(shuō):“沒(méi)有的事,你不要著急。”
柴草發(fā)潮,燒出滿棚黑煙。暮色漸漸上來(lái),暮色如煙,緩緩去籠罩水世界,水鳥齊著噪,一批批在小山上降落。奶奶顧不上吃飯,爺爺草草吃了幾口,滿肚里如塞了爛草,熬了半鍋燕麥魚片粥,終于冷成了團(tuán)。是夜,奶奶仍不時(shí)發(fā)陣痛,呻吟聲斷斷續(xù)續(xù),我父親有些固執(zhí),遲遲不肯落草。急得奶奶對(duì)我父親說(shuō):“孩子,你出來(lái)吧,別讓娘受洋罪啦。”爺爺坐在草鋪前,干著急幫不上忙,心里打著別種主意,說(shuō)話總難成句,斷斷續(xù)續(xù)如同打嗝,干脆就不說(shuō)話。淺黃的月色怯怯地上滿了棚,染著我爺爺青青的頭皮,染著我奶奶白白的身體。蟋蟀正在棚草上伏著,把翅膀摩得嚓嚓響。四處水聲喧嘩,像瘋馬群,如野狗幫,似馬非馬,似水非水,遠(yuǎn)了,近了,稀了,密了,變化無(wú)窮。我爺爺從草棚里望出去,見月光中亮出滿山野鳥,白得有些耀眼。山上生著一些毛栗子樹,東一棵西一棵,不像人工所為,樹不大,尚未到結(jié)果的年齡,白天已見到葉子上落滿了秋色,月下不見樹葉,恍惚間覺(jué)得樹上掛滿了異果,枝枝杈杈都彎曲下墜,把葉子搖得寒率響,細(xì)看才知樹上也全是大鳥。爺爺和奶奶都有些麻木,不知何時(shí)入睡。
翌日清晨,見半鍋冷粥已被老鼠舔得精光,棚內(nèi)還有數(shù)十匹盈尺的餓鼠在穿梭般跑動(dòng)。奶奶無(wú)心去顧群鼠,在鋪上輾轉(zhuǎn)反側(cè),臉上汗唏了,留下一道道痕跡。爺爺拿著棍子趕鼠,群鼠霸道兇惡,俱有跳梁之意,打死十幾匹后,才悻悻地退出棚去,散到小山各處覓食。水鳥們已飛去水面捕魚,山上樹上留下了它們的羽毛糞便,白白黑黑斑駁一片。日頭從黃水中初冒出來(lái)時(shí),血紅的一個(gè)大柿子,似乎戳一下就會(huì)流癟。后來(lái)東半邊水天一色,中間夾著個(gè)翻轉(zhuǎn)的徹底紅球。一會(huì)兒顯出金色來(lái),顯出銀色來(lái),形狀也由狼亢肥碩變得規(guī)矩玲瓏。日小水天闊。我爺爺查看了一下水勢(shì),見昨天插下的樹枝依然齊著水邊,水已平頭,不再見長(zhǎng),四周也沒(méi)有了那些張狂的大浪,水如平鏡,旋渦尚有,但都淺了。水上漂來(lái)許多雜物,一層層繞著土山。爺爺拿來(lái)一支長(zhǎng)柄鐵抓鉤,脫了光膀子,挺著一坨坨肉,沿著水邊打撈漂浮物。箱、柜、房梁、木架、浮樹、鐵桶,各色雜物在爺爺身后排成了隊(duì)。奶奶的叫聲已不響亮,一陣陣傳來(lái)。爺爺苦著臉,加緊干活,好像是要借此把心移開去。有些栗樹被洪水淹了,參差不齊地露出大大小小的冠,葉子全是死色了。在栗樹附近,爺爺看到一團(tuán)黑白不甚分明的東西在起伏,便鉚足了勁。一抓鉤扔過(guò)去,聽到水里噗噗響兩聲,水面上湮開兩片暗紅的顏色,用力拖過(guò)來(lái),我爺爺腸胃抽搐成團(tuán),吐出一口口黃水來(lái)。
爺爺用抓鉤拖上來(lái)一個(gè)死人。衣服縷縷片片地連著,露出脹鼓鼓的身體。死人挺直雙腿,十個(gè)腳趾頭用力張開,肚子已脹成氣球狀,臍眼深陷進(jìn)去。再往下看,見死人右手握拳,左手歪扭,只余拇指和食指,其他三指齊根沒(méi)了。死人脖子細(xì)長(zhǎng),肩胛處被爺爺?shù)淖ャ^鑿上兩個(gè)黑洞,洞里流出的污水把脖子弄臟了。死人下巴上有一圈花白的胡須,凌亂地糾葛在一起。嘴里兩排結(jié)實(shí)的黑牙齜出來(lái),上唇和下唇好像被水族吃掉了。鼻子還挺挺的似尖筍。左眼眶變成了一個(gè)深深的窟窿,里邊沉淀著淤泥,右眼球由一根雪白的筋絡(luò)掛到耳邊,黑白分明地看著世界。雙眉之間有一個(gè)圓圓的洞。頭發(fā)灰白相雜,頭皮皺得如吐盡絲的柞蠶。死人立刻招來(lái)了成群的蒼蠅并散發(fā)出撲鼻的惡臭。我爺爺閉著眼睛把死人捅下水去,不忍心再去打撈浮物,用力涮凈抓鉤,拄著,一路吐著,挨回了草棚。
奶奶已經(jīng)精疲力竭,躺著,如一條出水的大魚,時(shí)時(shí)做痙攣地一跳。見到爺爺進(jìn)棚,她慘淡一笑,說(shuō):“老三,你行行好,殺了我吧,我沒(méi)了勁,生不下你的孩子啦。”
我爺爺攥住我奶奶的手用力一握,兩個(gè)人眼里都盈出了淚水。爺爺說(shuō):“二小姐,是我把你害了。我不該把你帶到這里來(lái)。”奶奶的淚水流到臉上。奶奶說(shuō):“你別叫我二小姐。”爺爺看著奶奶,想起了往事。奶奶又發(fā)作起來(lái),一聲聲哭叫:“老三……行行好……給我一刀吧……”爺爺說(shuō):“二小姐,你不要往壞處想。你想想,我們能過(guò)到一塊,是多么樣地艱難。殺人時(shí)你給我遞刀,放火時(shí)你給我抱草,千萬(wàn)里路程,你一雙小腳也走了過(guò)來(lái),貓大個(gè)孩子你就生不下來(lái)他?”奶奶說(shuō):“我實(shí)在是一絲絲勁也沒(méi)有了。”爺爺說(shuō):“你等等,我弄飯給你吃。”
爺爺粗手大腳地煮了半鍋飯,盛滿了兩碗,一碗自己端著,一碗遞給奶奶。奶奶躺著有氣無(wú)力地?fù)u頭。爺爺惱起來(lái),把一碗飯用力摔出棚去,吼道:“好吧,要死大家一齊死!你死,孩子死,我也死!”說(shuō)完,不再看奶奶,見饑鼠在棚外如餓狼般爭(zhēng)斗。奶奶用力一躍,坐起來(lái),奪過(guò)一碗飯,用力吃起來(lái),一邊吃,一邊任淚水在腮上流。爺爺伸出大手,感動(dòng)地?fù)崦棠痰谋场?/p>
這一天我奶奶發(fā)了三個(gè)昏,傍晚時(shí),像死去一樣直挺挺仰在鋪上。爺爺守著奶奶,一身汗,滿臉淚,傍晚時(shí),深了眼窩長(zhǎng)了胡子,心里是一個(gè)混沌世界。
暮色漸漸滿了棚。土山上又飛來(lái)無(wú)數(shù)大鳥。
昨晚那樣蟋蟀振翅發(fā)聲,聲聲如泣如訴。
群鼠在棚外探頭探腦,小眼睛光亮如炭。
一大道凄涼月光射進(jìn)棚來(lái),罩住了我的爺爺和奶奶。我爺爺是個(gè)懔悍的男子漢,在陽(yáng)光里瞇起那兩只鷹隼樣的黑眼,下巴落在雙手里,身體彎曲成餓鷹狀,端的一個(gè)窮途英雄。我奶奶長(zhǎng)頸豐乳,修臂尖足,腹部高聳,腹中裝著我父親。我父親出生時(shí)很有些氣象,長(zhǎng)成后卻是個(gè)善良敦厚的農(nóng)民。陽(yáng)光從西邊下去,月光從東邊上來(lái),包著我的爺爺和奶奶,他們像洗過(guò)一樣的干凈。老鼠們?cè)囋囂教降剡M(jìn)棚來(lái),見我爺爺無(wú)動(dòng)靜,隨即猖獗起來(lái)。棚中的一切,在我爺爺眼里,都模糊腺朧。月光中的奶奶,舉手投足,似受傷的大鳥。水聲與水鳥的啁啾聲一浪浪襲來(lái)。交酉時(shí)了,我爺爺感到一陣涼氣襲背,不由得打了一個(gè)寒戰(zhàn),定睛看時(shí)。只見從那道月光里,蠢蠢地爬進(jìn)一個(gè)大物來(lái)。爺爺剛要發(fā)喊,就聽得那物發(fā)出人聲。女人聲:“大哥……救救我吧……”
爺爺慌忙起身,把一支寶貴的蠟燭點(diǎn)亮,跳動(dòng)的火苗下,那個(gè)女人正趴著喘氣。爺爺扶起她,讓她坐在一個(gè)草墩上,那女人像泡軟的泥巴,坐著,雙肩耷拉,脖子向兩邊歪,一頭黑發(fā),披散開蓋了肩,發(fā)間雜有亂草。她穿一身紫衣,緊貼住皮肉,兩個(gè)饅頭似的奶子僵冷光滑地挺著。長(zhǎng)眉吊眼,高鼻闊嘴,雙目分得很開。
“你是從哪里來(lái)的?”問(wèn)過(guò),爺爺立即知道問(wèn)得糊涂,渾身透濕,自然是水上來(lái)的。女人也不回答,腦袋枕在肩上,側(cè)身便倒。爺爺扶住她,聽到她喃喃地說(shuō):“……大哥,給我點(diǎn)東西吃……”
奶奶見到有人來(lái),暫時(shí)忘了自己,將身子收攏一下,讓爺爺把女人扶上鋪,換了濕衣,披上件奶奶的衣服,躺在奶奶身旁。爺爺去鍋里舀來(lái)一碗飯,用筷子挑著,一塊塊往那女人嘴里喂。那女人也不嚼,只管囫圇著咽,她的肚子里咕嚕嚕響,一碗飯,片刻就喂進(jìn)去。爺爺又盛來(lái)一碗飯。女人折身坐起來(lái),把衣服拉拉遮住身,接過(guò)碗筷,自己吃起來(lái)。爺爺和奶奶久未見人,初見如此虎狼般進(jìn)飯,心里暗暗生怕,不知這女人是人是鬼。吃過(guò)第二碗,女人用眼懇求地盯著爺爺。爺爺又為她端來(lái)一碗飯。吃相漸見和善。吃完三碗,我奶奶喊:“你不能再吃了!”女人吃驚地側(cè)目看著我奶奶,這才發(fā)現(xiàn)棚中尚有女人,便放下碗不再吃。眼里黑黑地放出光彩,怔了一會(huì),連聲道著謝。爺爺又問(wèn)了女人幾句話,她支支吾吾不想回答,也就不再問(wèn)。
奶奶又折騰開來(lái)。那女人一見奶奶的樣子,立刻就明白了。她站起來(lái),活動(dòng)了幾下腰腿,俯下身去摸了摸奶奶的肚子,那女人對(duì)著奶奶笑笑,也不說(shuō)話,從草鋪上抽出一把草,零零散散地撒在地上。接著像閃電一樣,女人彎腰從濕衣包里掏出一支烏黑的櫓子槍,一下子觸在我爺爺?shù)男馗稀E藢?duì)著我奶奶厲聲大喊:“站起來(lái)!要不我就打死他!”我奶奶一骨碌從草鋪上滾下來(lái),赤身裸體站在女人面前。
“彎下腰,把我撒到地下的草撿起來(lái),單棵單棵撿,撿一棵直一次腰。”女人命令道。我奶奶猶豫不決。女人說(shuō):“撿不撿?不撿我就開槍啦。”她橫眉立目,話出口如鋼豆落進(jìn)銅盆里,嘎崩利落脆。櫓子槍在燭光下一蹦一蹦地放光芒。
當(dāng)時(shí),我爺爺和我奶奶都像丟了魂魄,心里并不怎么害怕,鶻突蒙怔,猶如進(jìn)夢(mèng)。我奶奶彎下身子,一棵棵撿草,撿一棵送到鍋臺(tái)上,又撿一棵送到鍋臺(tái)上,起伏了四五十次,就見透明的羊水從腿間流下來(lái)。我爺爺漸漸醒神,炯炯地逼著女人,胸腔間出氣粗重。女人側(cè)目對(duì)我爺爺嫣然一笑,半個(gè)腮花紅月圓,低聲對(duì)我爺爺說(shuō):“別動(dòng)!”高聲對(duì)我奶奶說(shuō):“快撿!”
我奶奶終于把草撿完,哭著罵一句:“妖精!”
女人把櫓子槍收起來(lái),高笑幾聲,說(shuō):“別誤會(huì),我是醫(yī)生。大哥,你找來(lái)刀剪凈布,我給大嫂接生。”
我爺爺話都不會(huì)說(shuō)了,以為女人是仙女下凡。急急忙忙找來(lái)刀剪雜物,又遵囑刷鍋燒水,鍋蓋上冒出騰騰蒸氣。那女人出去涮凈自己衣褲。用力擰干,就在月光中換衣,我爺爺確確看見女人的身體素自如練,一片虔誠(chéng),如睹圖騰。水燒開,女人換好衣進(jìn)棚,對(duì)我爺爺說(shuō):“你出去吧。”
我爺爺在月下站著,見半月下銀光水面,時(shí)有透明嵐煙浮游天地間,聽著輕清水聲,更生出虔誠(chéng)心來(lái),竟屈膝跪倒,仰頭拜祝明月。
呱呱幾聲叫,從草棚中傳出來(lái)。我父親出世了,我爺爺滿臉掛淚沖進(jìn)草棚,見那女人正洗著手上血污。
“是個(gè)什么?”我爺爺問(wèn)。
“男孩。”女人說(shuō)。
我爺爺撲地跪倒,對(duì)女人說(shuō):“大姐,我今生報(bào)不了您的恩情,甘愿來(lái)世變狗變馬為您驅(qū)使。”
女人淡淡一笑,身子一歪,已經(jīng)睡成一個(gè)死人。爺爺把她搬上鋪,摸摸我奶奶,瞅瞅我父親,輕飄飄走出窩棚。月亮已上到中天,水里傳出大魚的聲音。
我爺爺循著水聲去找大魚,卻見一個(gè)橙黃色的漂浮物,正一聳一聳地對(duì)著土山撲過(guò)來(lái)。爺爺嚇了一跳,蹲下去,仔細(xì)地打量,見那物圓圓滑滑,嘩嘩啦啦撞得水響。愈來(lái)愈近,爺爺看到羊羔一樣的白色和炭一樣的黑色,黑推著白,把水面攪成銀鱗玉屑。
我父親降生后的第一個(gè)早晨,秋水包圍的土山上很是熱鬧。草棚里站著我爺爺,躺著我奶奶,睡著我父親,倚著女醫(yī)生,蹭著一個(gè)黑衣人,坐著一個(gè)自衣姑娘。
我爺爺夜里看到的漂浮物是一個(gè)釉彩大甕,甕里盛著白衣姑娘,黑衣人推著甕。
黑衣人個(gè)子短小,臉上少肉多骨,眼窩很深,白眼如瓷,雙耳像扇子一樣支棱著。他蹲著,鼻音重濁地說(shuō):“老弟,有煙嗎?我的煙全泡了湯了。”我爺爺搖搖頭說(shuō):“我有半年未聞到煙味了。”黑衣人打了一個(gè)呵欠,把脖子伸得很長(zhǎng),如一段黑木樁。在他黑木樁似的脖子上,套著兩根黑黑的線繩子,順著繩子往下看,便見腰里硬硬地別著家伙。黑衣人站起來(lái),伸了個(gè)大懶腰,我爺爺眼珠發(fā)硬,不轉(zhuǎn)地盯住黑衣人腰里那兩支盒子炮,手心里黏黏地滲出汗水。黑衣人低頭看看腰,齜出一嘴牙,很兇地一笑,說(shuō):“兄弟,弄點(diǎn)飯給吃吧,四海之內(nèi),都是兄弟朋友。我在水里泡了兩夜兩天,都是為了她。”
黑衣人指指那個(gè)端坐的白衣姑娘。她身軀挺大,卻是一張孩子的臉,五官生得靠,鼻梁如一條線,雙唇紅潤(rùn)小巧,雙眼大大的,毫無(wú)光彩,從摸摸索索的手上,才知道她是盲人。盲姑娘穿一身白綢衣,懷抱著一個(gè)三弦琴,動(dòng)作遲緩,悠悠飄飄,似夢(mèng)幻中人。
我爺爺往鍋里下了二升米、十條魚,點(diǎn)上火,讓白煙紅火從灶口沖出來(lái)。黑衣人咳嗽一聲,直著腰出了棚,從大甕里拎出一條口袋,倒出一堆黃銅殼子彈,擦著子彈屁股,一粒粒往梭子里壓。
那個(gè)自稱醫(yī)生的.紫衣女人年紀(jì)不會(huì)過(guò)二十五,她死睡了一夜,這會(huì)兒神清氣爽,兩只手把黑發(fā)扭成辮,倚在棚邊,冷冷地看著黑衣人的把戲。我爺爺忘不了她那支櫓子槍的厲害,眼睛在她腰間巡脧,竟不見一點(diǎn)鼓囊凸出之狀。一夜之間,山上出現(xiàn)這樣三個(gè)人物,殺過(guò)人的我爺爺也難免一顆心七上八下,燒著飯,猜著謎。奶奶體軟無(wú)力,看一會(huì)兒,索性閉上眼睛。
紫衣女人款款地走到盲女面前,蹲下去,細(xì)聲問(wèn):“妹妹,你從哪里來(lái)?”
“你從哪里來(lái)……你從哪里來(lái)……”盲女重復(fù)著紫衣女人的話,忽然開顏一笑,腮上顯出兩個(gè)大大的酒渦來(lái)。
“你叫什么名字?”紫衣女人又細(xì)聲問(wèn)。
盲女依然不答,臉上顯出甜透了的笑容來(lái),仿佛進(jìn)入了一個(gè)幸福美滿的遙遠(yuǎn)世界。
我父親響亮地哭起來(lái),沒(méi)有眼淚,也并不睜眼。奶奶把一個(gè)棕色奶頭塞進(jìn)他嘴里,哭聲隨即憋了。偶爾響一聲柴草燃燒的噼啪,更使遠(yuǎn)處的水聲深沉神秘。黑衣人全身沐著霞光,臉上脖子上如生了一層紅銹。金黃的子彈閃閃爍爍,不時(shí)把棚里人的視線吸出去。
紫衣女人姍姍地走出去,到黑衣人身邊,臉上露出似乎是羞怯之色,期期艾艾地問(wèn):“大叔,這是什么?”
黑衣人抬頭掃她一眼,獰笑著說(shuō):“燒火棍。”
“通氣嗎?”她傻乎乎地問(wèn)。
黑衣人手停頷揚(yáng),目光灼灼如云中電,尖縮的下巴上漾出獸般的笑紋,說(shuō):“你吹吹看!”
紫衣女人怯生生地說(shuō):“俺可不敢,吹到嘴里就拔不出來(lái)了。”
黑衣人滿臉狐疑地看著她,匆匆收好槍彈,站起來(lái),羅圈著腿,慢慢踱回棚里。棚里已溢出魚飯的香氣。
只有兩只碗。盛滿兩碗飯,我爺爺雙手端起一碗,敬到紫衣女人面前。我爺爺說(shuō):“大姐,請(qǐng)用飯。窮家野居,沒(méi)有好的給您吃。等洪水下去,我再想法謝您。”女人瞇起眼,笑著把碗接過(guò)去,遞給我奶奶,說(shuō):“大嫂才是最辛苦的,你該去抓些魚來(lái),煨湯給她吃,鯉魚補(bǔ)陽(yáng),鯽魚發(fā)奶。”我奶奶淚眼婆娑地接過(guò)碗,嘴唇抖著,卻說(shuō)不出話,低下頭時(shí),將一顆淚珠落在我父親臉上。我父親睜開了兩只黑眼,懶洋洋地看著光線中浮游的纖塵。
爺爺又端起一碗飯,看了一眼黑衣人,道著歉:“大哥,委屈您等一會(huì)兒。”爺爺把碗往紫衣女人面前送。黑衣人從半空中伸出一只手,把飯碗托了過(guò)去,臉上透出冷笑來(lái)。爺爺壓住不快,把懊惱變成咳嗽,一頓一頓地吐出來(lái)。
黑衣人搶過(guò)飯碗,自己并不吃。他蹲在盲女面前,左手端碗,右手持筷,挑起飯來(lái),一坨一坨地往盲女嘴里搗。盲女雙手接著三弦琴,脖子伸得舒展,下巴微揚(yáng),像待哺的雛燕。她一邊吃,一邊用手指撥弄著琴弦布冷冬布冷冬地響。
連喂了盲女兩碗飯,黑衣人微微氣喘。舉起衣袖給盲女擦凈嘴,他轉(zhuǎn)過(guò)身,把碗扔到紫衣女人面前,說(shuō):“小姐,該您啦。”紫衣女人說(shuō):“也許該讓你先吃。”黑衣人說(shuō):“無(wú)功無(wú)德,后吃也罷。”紫衣女人說(shuō):“你當(dāng)心走了火。”
爺爺對(duì)黑衣人講紫衣女人昨晚的事,意在讓他明白些事理。黑衣人冷笑不止。爺爺問(wèn):“你笑什么?你以為我在騙你?”黑衣人斂容答道:“怎么敢!不過(guò),也沒(méi)有什么稀奇,人來(lái)世上走一遭,多多少少都有些絕活。”爺爺說(shuō):“我就沒(méi)絕活。”黑衣人說(shuō):“有的,你會(huì)有的。沒(méi)有絕活,你何必在這莽蕩草洼里混世。”
黑衣人說(shuō)著話,見有幾匹大鼠聞到飯味,在棚外探頭探腦。他嘴不停話,手伸進(jìn)腰間,拖出一支盒子炮,叭叭兩聲脆響,槍口冒出藍(lán)煙,棚內(nèi)溢開火藥味,有兩匹鼠涂在棚口,白的紅的濺了一圈。我奶奶驚得把碗扔了,我爺爺也瞠目。紫衣女人青眼逼視黑衣人。我父親鼾鼾地睡覺(jué)。盲女布冷冬布冷冬地彈著弦子。我爺爺發(fā)作起來(lái),吼道:“你這人好沒(méi)道理!”,黑衣人大笑起來(lái),搖搖晃晃起身,站在鍋前,用一柄鍋鏟子挖著飯,旁若無(wú)人地吃起來(lái)。吃飽,半句客氣話也沒(méi)有,彎腰拍拍盲女的頭,牽了她一只手,踉蹌著出門去。把盲女安頓在陽(yáng)光下曬著,從腰里拖出雙槍,玩笑般射著土山周圍水面上那些嬉戲覓食的大鳥。他每發(fā)必中,水面上很快浮起十幾具鳥尸,紅血一圈圈地散漫。群鳥驚飛,飛到極高極遠(yuǎn)處,仍有中彈者直直地墜落,砸紅一塊水面。
紫衣女人臉色灰白,漸漸地逼近了黑衣人。黑衣人不睬她,黑臉對(duì)著陽(yáng)光,泛出鋼鐵顏色。他似念似唱,和著白衣盲女布冷冬布冷冬的弦子:“綠螞蚱。紫蟋蟀。紅蜻蜒。白老鴰。藍(lán)燕子。黃鵲鴿。”“你一定是大名鼎鼎的老七!”紫衣女人說(shuō)。“我不是老七。”黑衣人瞥她一眼,說(shuō)。“不是老七哪有這等神槍?”黑衣人把雙槍插進(jìn)腰問(wèn),舉起十指健全的雙手說(shuō):“你看看,我是老七嗎?”他往水里射去一口痰,有小魚兒飛快圍上去。“干女兒,接著我唱的往下唱呀,”他對(duì)白衣盲女說(shuō),“唱呀,白老鴰。藍(lán)燕子。黃鵲鴿——”
盲女微微笑,唱起來(lái),童音猶存,天真動(dòng)人:“綠螞蚱吃綠草梗。紅蜻蜓吃紅蟲蟲。紫蟋蟀吃紫莽麥。”
“你是說(shuō),老七七個(gè)指頭?”紫衣女人問(wèn)。
黑衣人說(shuō):“七個(gè)指頭是老七,十個(gè)指頭不是老七。”
“白老鴰吃紫蟋蟀。藍(lán)燕子吃綠螞蚱。黃鵲鴿吃紅蜻蜓。”
“你這樣好槍法,在高密縣要數(shù)第一。”“我不如老七,老七能槍打飛蠅,我不能。”“老七呢?”“被我除了。”
“綠螞蚱吃白老鴰。紫蟋蟀吃藍(lán)燕子。紅蜻蜒吃黃鵲鴿。”
陽(yáng)光落滿了土山。水鳥逃竄后,水面輝煌寧?kù)o,那些半淹的小栗樹一動(dòng)不動(dòng)。紫衣女人搓搓手,不知從什么地方閃電般跳進(jìn)手里一支檐子槍,對(duì)準(zhǔn)黑衣人就摟了火,子彈打進(jìn)黑衣人的胸膛。他一頭栽倒,慢慢地翻過(guò)身,露出一個(gè)愉快的笑臉:“……侄女……好樣的……你跟你娘像一個(gè)模子脫的……”紫衣女人哭叫著:“你為什么要害死我爹?”黑衣人用力抬起一個(gè)手指,指著白衣盲女,喉嚨里響了一聲,便垂手撲地,腦袋側(cè)在地上。
來(lái)了一只黑毛大公雞,伸著脖子叫:“哽哽哽——噢——”盲女還在彈著弦子唱。
洪水開始落了。
我很小的時(shí)候,爺爺教給我一支兒歌:
綠螞蚱。紫蟋蟀。紅蜻蜓。
白老鴰。藍(lán)燕子。黃鶴鴿。
綠螞蚱吃綠草梗。紅蜻蜓吃紅蟲蟲。
紫蟋蟀吃紫蕎麥。
白老鴰吃紫蟋蟀。藍(lán)燕子吃綠螞蚱。
黃鶴鎢吃紅蜻蜒。
綠螞蚱吃白老鴰。紫蟋蟀吃藍(lán)燕子。
紅蜻蜓吃黃鶴鵠。
來(lái)了一只大公雞,伸著脖子叫“哽哽哽——
嗔——”
讀莫言的作品有感
讀莫言的作品有感
莫言筆下的《紅高粱》經(jīng)歷了歲月洗禮,在塵土泥垢的孕育中,在雨露甘霖的滋潤(rùn)下,如今早已熟透,不僅顆粒滿倉(cāng),而且還浸透著十里紅的酒香。這部作品痛快淋漓的歌頌人性魅力,用純粹的語(yǔ)言元素禮贊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悲催的情節(jié)中滲透著生與死的較量,揮灑著血肉與靈魂的抗?fàn)帯Mㄟ^(guò)實(shí)物與意念的有效結(jié)合,色彩與空間的神秘量化,使得小說(shuō)的字里行間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透露著對(duì)莊嚴(yán)生命的向往與期盼。
還記得看到羅漢大叔被日本人活活剝皮而死的一幕時(shí),我的內(nèi)心充滿了對(duì)侵略者的仇恨。我想,這就是小說(shuō)給予人類的民族力量,情感歸向,使奮身抵抗,贏得生命解放的偉大理念根深蒂固的扎根在中國(guó)人民的心中。
而今,再見莫言已經(jīng)是27年后的今天,他憑借著《豐乳肥臀》、《蛙》、《檀香刑》、《生死疲勞》等作品,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中國(guó)籍作家,自此中國(guó)小說(shuō)在國(guó)際文學(xué)舞臺(tái)上呈現(xiàn)出了更為立體而生動(dòng)的形象。
莫言的寫作文風(fēng)大膽豪邁,其思路天馬行空,語(yǔ)言張弛有度,人物形象鮮明飽滿,他的作品大多充滿了濃濃的鄉(xiāng)土氣息。用原生態(tài)的鄉(xiāng)土人情填平千溝萬(wàn)壑的華夏大地,用魔幻而具有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筆觸書寫多災(zāi)多難的齊魯山河,成為這位“尋根作家”最能打動(dòng)人心的運(yùn)筆利器。
近日來(lái)又看過(guò)莫言的兩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生死疲勞》和《檀香刑》,給我的感覺(jué)是他仍然沒(méi)有改變筆下大多數(shù)小說(shuō)的統(tǒng)一特色,那就是作品往往都充滿了顆粒般的血腥感。無(wú)論人物是在痛苦中輪回,還是在屈辱中茍且偷生,他們都經(jīng)歷過(guò)撕心裂肺、痛徹心扉的“痛”。盡管其中有兩情相悅、忠貞不渝的愛(ài)戀,可仍舊改變不了貫穿在作品當(dāng)中以“悲慘”為主線的鮮明特點(diǎn),以強(qiáng)調(diào)“頑強(qiáng)生命力”為主要基調(diào)的顯著特征。
《生死疲勞》的主人公靠脫胎轉(zhuǎn)世脫離現(xiàn)世的悲歡,卻擺脫不了世代輪回中風(fēng)水輪流轉(zhuǎn)的時(shí)運(yùn)。只有通過(guò)驢、牛、豬、狗、猴,五種動(dòng)物的眼睛來(lái)描繪苦大仇深的農(nóng)民終于獲得屬于自己的土地,卻還沒(méi)來(lái)得急好好耕作的時(shí)候,又陷入了一個(gè)扭曲變形的動(dòng)蕩時(shí)期。在感嘆中國(guó)土地變遷史龐大復(fù)雜的同時(shí),又不得不承認(rèn)歷史的畸形錯(cuò)位。值得一提的是人們并沒(méi)有因?yàn)檫@紛至沓來(lái)仿若苦難而打倒,而是倔強(qiáng)、固執(zhí)的活下去,去欣賞豐沛土地的日新月異,來(lái)等待人類脫胎換骨后重獲新生的消息。當(dāng)男主人公西門鬧終于從“六道輪回”中轉(zhuǎn)世為人后,苦難與不公依然緊緊纏繞著他的身體,但是轉(zhuǎn)世為人的快樂(lè)終究讓他忘記了身為牲畜時(shí)的屈辱與離奇,無(wú)論如何能做一個(gè)直立行走的人總是要比四腳爬行的牲畜好很多。作者熱愛(ài)這片安生立命的土地,所以才讓自己的思緒在陰陽(yáng)兩界間游刃有余肆意穿行,用牲畜的狂歡來(lái)加深對(duì)人民苦難的理解,用激情與不屈期待新世紀(jì)鐘聲的響起,用釋然與寬恕來(lái)安慰已經(jīng)逝去和仍然存在的靈魂。
在《檀香刑》中,孫柄是錢縣令相好媚娘的父親,他們之間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糾葛。在孫柄的親人被德國(guó)人殘害后,他決心遠(yuǎn)走他鄉(xiāng)去投靠義和團(tuán),而后帶領(lǐng)自己的隊(duì)伍回鄉(xiāng)報(bào)仇雪恨,毀壞德國(guó)人修建的鐵路被抓后,錢縣令在幾番內(nèi)心爭(zhēng)斗中,終于不惹看到在殘酷刑罰的摧殘下生不如死的孫柄再受熬煎,揮劍刺死這位懷有深仇大恨而抵制德國(guó)入侵者的民族英雄。是怎樣錯(cuò)落的情感才能讓清廷的政府官員放棄高官厚祿,封侯拜相的大好機(jī)會(huì),寧愿把自己也置身險(xiǎn)地;是怎樣的利益驅(qū)使,讓清朝官府在外侵者面前趨炎附勢(shì),把殘殺同胞、對(duì)其施加酷刑當(dāng)做取樂(lè)的手段。這部小說(shuō)中的人物生活在那個(gè)特定的年代里,注定他們的命運(yùn)只能是沉重的,但是沒(méi)有人能遮掩住歷史的血圖騰,因?yàn)槟鞘怯蒙碥|換來(lái)的麻木、冷漠、壓抑、無(wú)助與掙扎的洗禮。
有人批判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是因?yàn)樵g毀了中國(guó)人的形象,成為外國(guó)人取笑中國(guó)人文歷史的話題。雖然人人都可以發(fā)表自己真實(shí)的閱讀感受,可是我們要正視中國(guó)的歷史。莫要言說(shuō)小說(shuō)歷史背景的真與假,莫要言說(shuō)其中人物的好與壞,單憑莫言能夠大膽果敢的寫出中國(guó)改革開放60年來(lái),人們對(duì)土地的深情與熱愛(ài),就不該把中國(guó)人的驕傲踐踏在腳下。他沒(méi)有跟風(fēng)時(shí)代的喜好,迎合大眾的需求,標(biāo)榜自己的英雄主義,只是想盡可能的描寫出斑斕壯闊、波瀾起伏的中國(guó)歷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