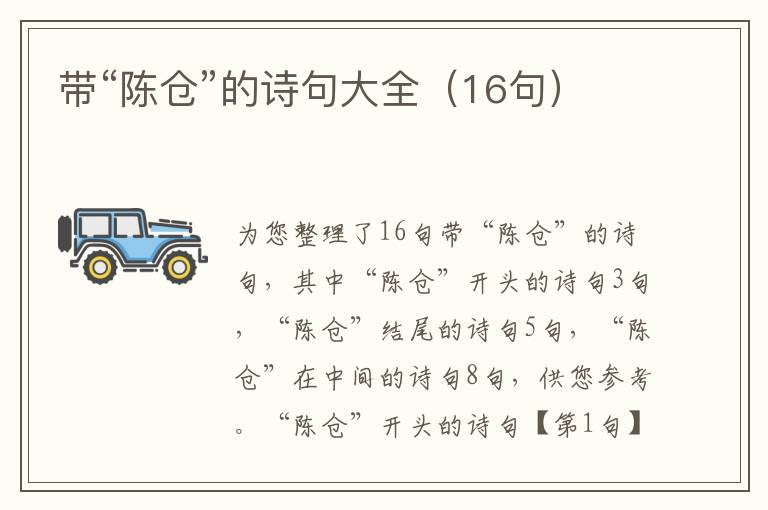老舍描寫北平的句子合集90句

老舍的北平隨筆
家鄉,一個帶著絲絲繾綣溫存的詞匯,我們愛它的一草一木、一樹一花,感受拂曉日暮,歷經春夏秋冬,它有不足,但始終是扎根的地方。葉,怎能不愛它的根呢?我們終歸,在心里愛著它,這份愛,無法言說,就像老舍在《想北平》中寫的那樣:“可是,我真愛北平。這個愛幾乎是想說而說不出的。我愛我的母親。怎樣愛?我說不出。”
老舍,生于北平,眠于北平,這個偉大卓越的作家用眾多作品,詮釋了“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想北平》以樸素平實的語言描繪了一個古色古香的北平,在他的筆下,北平時而充滿古玩文物的墨氣,時而充滿瓜果蔬菜的清香,即使是歐洲四大“歷史的都城”倫敦、巴黎、羅馬、堪司坦丁堡也比不上這座古城。
他說:“真愿成為詩人,把一切好聽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鵑似的啼出北平的俊偉。”北平孕育了老舍,它早已成為深入骨髓、與心靈相連的思念,離不開,忘不了。老舍最終沉于太平湖,永遠與北平融為一體。
《想北平》的開頭提到:
如果讓我寫一本小說,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為我可以撿著我知道的寫,而躲開我所不知道的。
的確,老舍這樣做了,他以北平為背景創作了長篇小說《駱駝祥子》,與散文不同的是,小說中除去了日常生活的氣息,用濃厚的藝術風格形式,刻畫了一個堅硬殘酷的.北平,沒有古玩文物,沒有瓜果蔬菜,有的只是社會底層貧苦市民用血汗染成的故事。
《駱駝祥子》中的眾多環境描寫,蘊含著一種被壓抑的嘶吼,灰色黯淡,為后文作鋪墊,從而進一步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資產階級對勞動者的壓迫與剝削。
云還沒有鋪滿了天,地上已經很黑,極亮極熱的晴午忽然變成黑夜似的。風里帶著雨星,像在地上尋找著什么似的,東一頭西一頭的亂撞。北邊遠處一個紅閃,像把黑云掀開一塊,露出一大片血紅似的。
這是祥子生病之前一段對天空自然環境的描寫,細致地展現了暴風雨襲來的景象,像是金戈鐵馬的戰爭,一觸即發。如此惡劣的天氣,仿佛正在預示祥子之后生活的坎坷與困苦,不禁令人心寒與哀傷。
也許這就是北平的另一面,這就是社會的另一面,“它污濁,它美麗,它衰老,它活潑,它雜亂,它安閑,它可愛,它是偉大的夏初的北平”。它是老舍筆下凜冽鋒利的都城,也是心中愛著念著的家鄉,它是與老舍血肉相連的北平。
老舍: 北平的中秋
中秋節是團圓的節日,那么在作家老舍先生的眼里,北平的中秋是怎樣的呢?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麗的時候。天氣正好不冷不熱,晝夜的長短也劃分得平勻。沒有冬季從蒙古吹來的黃風,也沒有伏天里挾著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藍,那么亮,好像是含著笑告訴北平的人們:在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會給你們什么威脅與損害的。西山北山的藍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還披上各色的霞帔。
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攤與地攤,和果店里,都陳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來的水果。各種各樣的葡萄,各種各樣的梨,各種各樣的蘋果,已經叫人夠看夠聞夠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聞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蘆形的大棗,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紅那樣大的白海棠,還有只供聞香兒的海棠木瓜,與通體有金星的香檳子,再配上為拜月用的,貼著金紙條的枕形西瓜,與黃的紅的雞冠花,可就使人顧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經辨不清哪一種香味更好聞,哪一種顏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那些水果,無論是在店里或攤子上,又都擺列的那么好看,果皮上的白霜一點也沒蹭掉,而都被擺成放著香氣的立體的圖案畫,使人感到那些果販都是些藝術家,他們會使美的東西更美一些。況且,他們還會唱呢!他們精心的把攤子擺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調的“果贊”:“唉——一毛錢兒來耶,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兒,皮兒又嫩,水兒又甜,沒有一個蟲眼兒,我的小嫩白梨兒耶!”歌聲在香氣中顫動,給蘋果葡萄的靜麗配上音樂,使人們的腳步放慢,聽著看著嗅著北平之秋的'美麗。
同時,良鄉的肥大的栗子,裹著細沙與糖蜜在路旁唰啦唰啦的炒著,連鍋下的柴煙也是香的。“大酒缸”門外,雪白的蔥白正拌炒著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兩肉,有兩三毛錢就可以混個醉飽。高粱紅的河蟹,用席簍裝著,沿街叫賣,而會享受的人們會到正陽樓去用小小的木錘,輕輕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腳。
同時,在街上的“香艷的”果攤中間,還有多少個兔兒爺攤子,一層層的擺起粉面彩身,身后插著旗傘的兔兒爺——有大有小,都一樣的漂亮工細,有的騎著老虎,有的坐著蓮花,有的肩著剃頭挑兒,有的背著鮮紅的小木柜;這雕塑的小品給千千萬萬的兒童心中種下美的種子。
同時,以花為糧的豐臺開始一挑一挑的往城里運送葉齊苞大的秋菊,而公園中的花匠,與愛美的藝菊家也準備給他們費了半年多的苦心與勞力所養成的奇葩異種開“菊展”。北平的菊種之多,式樣之奇,足以甲天下。
同時,像春花一般驕傲與俊美的青年學生,從清華園,從出產蓮花白酒的海甸,從東南西北城,到北海去劃船;荷花久已殘敗,可是荷葉還給小船上的男女身上染上一些清香。
同時,那文化過熟的北平人,從一入八月就準備給親友們送節禮了。街上的鋪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種餡子的月餅,把自己打扮得像鮮艷的新娘子;就是那不賣禮品的鋪戶也要湊個熱鬧,掛起秋節大減價的綢條,迎接北平之秋。
北平之秋就是人間的天堂,也許比天堂更繁榮一點呢!
——節選自〈四世同堂〉
老舍《北平的夏天》欣賞
【老舍《北平的夏天》原文】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愛的。從十三陵的櫻桃下市到棗子稍微掛了紅色,這是一段果子的歷史——看吧,青杏子連核兒還沒長硬,便用拳頭大的小蒲簍兒裝起,和“糖稀”一同賣給小姐與兒童們。慢慢的,杏子的核兒已變硬,而皮還是綠的,小販們又接二連三的喊:“一大碟,好大的杏兒嘍!”這個呼聲,每每教小兒女們口中饞出酸水,而老人們只好摸一摸已經活動了的牙齒,慘笑一下。不久,掛著紅色的半青半紅的“土”杏兒下了市。而吆喝的聲音開始音樂化,好象果皮的紅美給了小販們以靈感似的。而后,各種的杏子都到市上來競賽:有的大而深黃,有的小而紅艷,有的皮兒粗而味厚,有的核子小而爽口——連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馳名的“白杏”用綿紙遮護著下了市,好象大器晚成似的結束了杏的季節。當杏子還沒斷絕,小桃子已經歪著紅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見了。各樣的桃子,圓的,扁的,血紅的,全綠的,淺綠而帶一條紅脊椎的,硬的,軟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來到北平給人們的眼,鼻,口,以享受。紅李,玉李,花紅和虎拉車,相繼而來。人們可以在一個擔子上看到青的紅的,帶霜的發光的,好幾種果品,而小販得以充分的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氣吆喝出一大串兒來——“買李子耶,冰糖味兒的水果來耶;喝了水兒的,大蜜桃呀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來耶……”
每一種果子到了熟透的時候,才有由山上下來的鄉下人,背著長筐,把果子遮護得很嚴密,用拙笨的,簡單的呼聲,隔半天才喊一聲:大蘋果,或大蜜桃。他們賣的是真正的“自家園”的山貨。他們人的樣子與貨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邊與北邊的青山上的果園,而感到一點詩意。
梨,棗和葡萄都下來的較晚,可是它們的種類之多與品質之美,并不使它們因遲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們的大白棗,小白梨與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棗,人們便有“一葉知秋”之感,而開始要曬一曬夾衣與拆洗棉袍了。
在最熱的時節,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時節。果子以外還有瓜呀!西瓜有多種,香瓜也有多種。西瓜雖美,可是論香味便不能不輸給香瓜一步。況且,香瓜的分類好似有意的“爭取民眾”——那銀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適于文雅的仕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綠皮金黃瓤子的“三白”與“哈蟆酥”就適于少壯的人們試一試嘴勁,而“老頭兒樂”,顧名思義,是使沒牙的老人們也不至向隅的。
在端陽節,有錢的人便可以嘗到湯山的嫩藕了。趕到遲一點鮮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錢的,也可以嘗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覆著張嫩荷葉,葉上托著鮮菱角,鮮核桃,鮮杏仁,鮮藕,與香瓜組成的香,鮮,清,冷的,酒菜兒。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們,不是還可以買些菱角與雞頭米,嘗一嘗“鮮”嗎?
假若仙人們只吃一點鮮果,而不動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應當是北平啊!
天氣是熱的,可是一早一晚相當的涼爽,還可以作事。會享受的人,屋里放上冰箱,院內搭起涼棚,他就會不受到暑氣的侵襲。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蓮塘里去劃船,或在太廟與中山公園的老柏樹下品茗或擺棋。“通俗”一點的,什剎海畔借著柳樹支起的涼棚內,也可以爽適的吃半天茶,咂幾塊酸梅糕,或呷一碗八寶荷葉粥。愿意灑脫一點的,可以拿上釣竿,到積水灘或高亮橋的西邊,在河邊的古柳下,作半日的垂釣。好熱鬧的,聽戲是好時候,天越熱,戲越好,名角兒們都唱雙出。夜戲散臺差不多已是深夜,涼風兒,從那槐花與荷塘吹過來的涼風兒,會使人精神振起,而感到在戲園受四五點鐘的悶氣并不冤枉,于是便哼著《四郎探母》什么的高高興興的走回家去。天氣是熱的,而人們可以躲開它!在家里,在公園里,在城外,都可以躲開它。假若愿遠走幾步,還可以到西山臥佛寺,碧云寺,與靜宜園去住幾天啊。就是在這小山上,人們碰運氣還可以在野茶館或小飯鋪里遇上一位御廚,給作兩樣皇上喜歡吃的菜或點心。
【老舍簡介】
老舍,中國小說家、劇作家。生于1899年,卒于1966年,滿族,祖籍北京。原名舒慶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
老舍的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駱駝祥子》、《趙子日》、《老張的哲學》、《四世同堂》、《二馬》、《小坡的生日》、《離婚》、《貓城記》、《正紅旗下》,劇本《殘霧》、《方珍珠》、《面子問題》、《龍須溝》、《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戲劇集》、《柳樹井》、《女店員》、《全家福》、《茶館》,報告文學《無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火車集》、《貧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梁實秋《北平的零食小販》賞讀
北平人饞。饞,據字典說是“貪食也”,其實不只是貪食,是貪食各種美味之食。美味當前,固然饞涎欲滴,即使閑來無事,饞蟲亦在咽喉中抓撓,迫切的需要一點什么以膏饞吻。三餐時固然希望膏粱羅列,任我下箸,三餐以外的時間也一樣的想饞嚼,以鍛練其咀嚼筋。看鷺鷥的長頸都有一點羨慕,因為頸長可能享受更多的徐徐下咽之感,此之謂饞,饞字在外國語中無適當的字可以代替,所以講到饞,真“不足為外人道”。有人說北平人之所以特別饞,是由于當年的八旗子弟游手好閑的太多,閑就要生事,在吃上打主意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各式各樣的零食小販便應運而生,自晨至夜逡巡于大街小巷之中。
北平小販的吆喝聲是很特殊的。我不知道這與平劇有無關系,其抑揚頓挫,變化頗多,有的豪放如唱大花臉,有的沉悶如黑頭,又有的清脆如生旦,在白晝給浩浩欲沸的市聲平添不少情趣,在夜晚又給寂靜的夜帶來一些凄涼。細聽小販的呼聲,則有直譬,有隱喻,有時竟像謎語一般的耐人尋味。而且他們的吆喝聲,數十年如一日,不曾有過改變。我如今閉目沉思,北平零食小販的呼聲儼然在耳,一個個的如在目前。現在讓我就記憶所及,細細數說。
首先讓我提起“豆汁”。綠豆渣發酵后煮成稀湯,是為豆汁,淡草綠色而又微黃,味酸而又帶一點霉味,稠稠的,混混的,熱熱的。佐以辣咸菜,即棺材板切細絲,加芹菜梗,辣椒絲或末。有時亦備較高級之醬菜如醬蘿卜醬黃瓜之類,但反不如辣咸菜之可口,午后啜三兩碗,愈吃愈辣,愈辣愈喝,愈喝愈熱,終至大汗淋漓,舌尖麻木而止。北平城里人沒有不嗜豆汁者,但一出城則豆渣只有喂豬的份,鄉下人沒有喝豆汁的。外省人居往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養成喝豆汁的習慣。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
其次是“灌腸”。后門橋頭那一家的大灌腸,是真的豬腸做的,遐邇馳名,但嫌油膩。小販的灌腸雖有腸之名實則并非是腸,僅具腸形,一條條的以芡粉為主所做成的橛子,切成不規則形的`小片,放在平底大油鍋上煎炸,炸得焦焦的,蘸蒜鹽汁吃。據說那油不是普通油,是作房里從馬肉等熬出來的油,所以有這一種怪味。單聞那種油味,能把人惡心死,但炸出來的灌腸,噴香!
從下午起有沿街叫賣“面筋喲!”者,你喊他時須喊“賣熏魚兒的!”他來到你門口打開他的背盒由你檢選時卻主要的是豬頭肉。除豬頭肉的臉子、口條之外還有腦子、肝、腸、苦腸、心頭、蹄筋等等,外帶著別有風味的干硬的火燒。刀口上手藝非凡,從夾板縫里抽出一把飛薄的刀,橫著削切,把豬頭肉切得片薄如紙,塞在那火燒里食之,熏味撲鼻!這種鹵味好像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在煨煮熏制中有特殊的風味,離開北平便嘗不到。